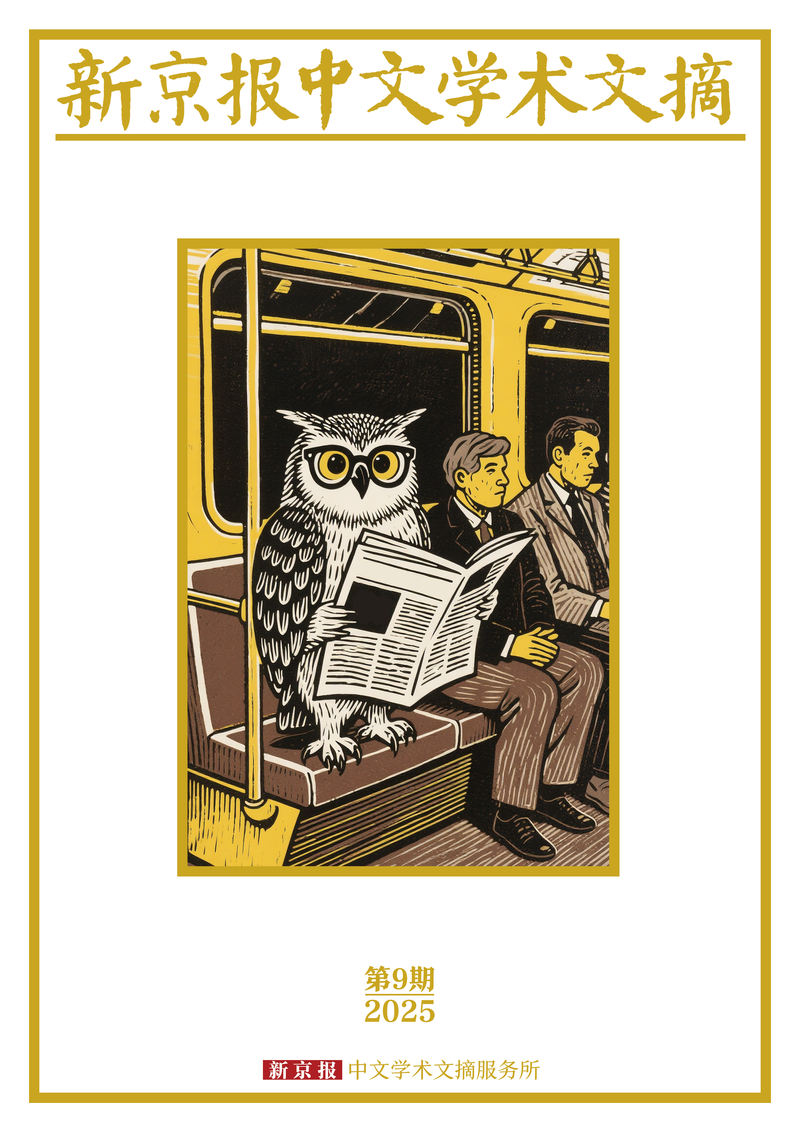 “随着现代技术和常识的进步并在复杂的关系中竞争,常识的界限正在不断变化。” ——吴非:《论常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第172-183页,第192页。本期审阅:陈新宇黄殿林文字摘录:罗东在现代,除了书籍之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另一个基本手段。今年8月以来,《京报书评周刊》拓展了以书评为基础的“学术评论与摘要”的知识传播工作,并筹办了“京报中文学术摘要服务”,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杂志界和《人大报纸资料复印》、《社会科学摘要》等摘要刊物提供服务。每周出版一期,每期推荐两篇文章。每期均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最新、专业、前沿的文章。我们也希望入选的文章具有清晰的本土和全球问题意识,具有独特的中文写作气质。这是第九次了。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吴飞分析了常识与司法判决的关系。根据常识的理解,常识是常识,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或某一特定专业内的大多数专业人士)认可的不言自明的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案件的处理结果明显违背一定程度的常识时,通常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民群众对正义的期望。常识是社会的基础。除了支持司法判决外,还有o 对其使用的限制。笔者以辩证的态度、谨慎的态度来分析两者的关系。以下内容经社会科学许可转载。请参阅原始出版物的摘要、表格、参考文献和注释。作者 |剧照来自吴非的电视剧《以法律之名》(2025)。常识作为日常社会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了基本认识,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化程度。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常识构成了人们在社会经验问题上趋于达成共识的重要认知基础,是主体间性的关键要素。在司法领域,常识也构成公众对司法稳定期望的认知基础和心理。司法判决必须始终符合常识。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判决结果仍然与事实相矛盾。符合常识或明显偏离常识。此前,鄂尔多斯“贵毛衣事件”和天津赵华非法持有武器事件曾引发争议。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在一起行人碰撞案件纠纷中使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表述,引发广泛质疑。法院随后发布了现场视频并道歉以平息争议。学者们将这种特殊情况称为“反常识”或“后常识”现象。从案件判决的整体社会影响来看,“有悖常理”现象的出现,强烈影响了司法预期的稳定性。学者们针对这些类型的问题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在此过程中,他们卓有成效地探讨了如何避免常识的认知偏差,并就常识的作用和重要价值达成了共识。司法决策中的nse。需要注意的是,案件违反常识并不一定意味着法院判决本身就是错误的。从其规范性来看,常识作为知识体系是基础性的、普遍性的,而对具体案件的调查则必须是具体的、具体的。两者之间永远存在天然的差距。再者,每个人都有常识,但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培养。它可以改变。因此,当出现共识问题时,单方面批评司法判决可能过于短视。本文旨在强调常识与司法判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常识,增加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具体来说,如果常识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它是否可以在司法程序中受到质疑和审查?不同级别的c如何常识有利于司法判决规范的形成吗?在司法判决中运用常识的条件和限制是什么?但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和研究。一、常识的内容层次和基本性质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将其与常识、常理一起使用,但其含义与“理”的概念几乎相同。相比于常识和常识的语境依赖,常识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恒定性,其稳定司法预期的作用更加明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常识很容易适用于司法实践;有些常识是基于人们的经验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些常识却是有争议的,这使得法院案件的处理更加复杂化,并引发了常识之争。常识的这些复杂属性源自其具体内容。因此,深探讨常识的内容层次和基本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常识在司法裁判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性。 (一)常识的内容层面 常识作为一个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中国经典中有一个词叫“common sense.n”,基本意思是日常知识。现代意义上的“common sense”一词一般认为是日本明治时期创造的新词,19世纪末传入中国并吸收到汉语中。根据《汉语词典》的定义,common sense是指一般知识。汉语中使用的“一般生活经验”、“一般规则”、“公序良俗”等概念中也包含常识。常识的概念是commonsense,源自sensuscommunis,指的是主要以感觉为基础的共同情感和意识。到了现代,它已经成为一个指代人类认知能力的概念,其含义几乎等同于智慧、智慧、理性和实用主义。陈家英教授认为,中文的“common sense”重在表面的事实,而英文的“common sense”重在事实中蕴含的真理。常识通常与对非凡事实和深刻真理的理解有关,特别是与理论知识和理论体系有关。 《比较法视角下的证据制度》 作者:【美国】Mirjan R. Damaska 译者:吴红耀、韦晓才等版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常识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取决于其内容被学习、加工和内化的程度。第一层次也是肤浅的层次,其中知识,尤其是事实,表现为关于某事物的一些知识。他们来自p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历,属于“经验知识”。第二个层次的常识是基于上述知识总结出来的一系列原理和判断。这些判断是基于对事实的一般和共同理解。如果判断的专业性和深刻性很高,那么它就不属于常识的范畴。第三个层次可以理解为在常识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意识”的含义由此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识为社会个体成员与外界之间的精神沟通和价值认同提供了条件。当然,这个常识水平是相对的。 “当谈到人类生活的事实时,很难有简单的事实。事实和社会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生活的事实最初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创造的。” 《论可能的生活》作者:Zh敖汀阳版:生活/阅读/新知 三联书店2024年9月 社会人们普遍理解和认可的道理,是在掌握基本常识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有些已经属于常识的判断本身就是常识。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用词来看,司法文书中通常不区分常识和常识含义。然而,当用于评估行为时,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异。常识侧重于从理性的角度评价人们的行为,而常识则侧重于从认知的角度评价人们的行为。常识评估更为基础。一般来说,表层常识构成了人们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而判断意义上的常识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调节作用则更为突出。常识为人们建立基本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说,人们不仅遵守常识,而且也期望别人遵守常识。换句话说,违反常识就被认为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深刻的常识,即思想意识和良心意识的常识,是评价司法判决整体价值的指南。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是由特定社会所接受的一套信念组成的,并且该社会的成员假设这些信念是所有理性人所共有的。这些不同层次的知识和原则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智慧,是公众形成的最普遍的经验,也是所有文化中最共同、稳定、流行的要素。除了内容的层次之外,常识的范围也受到限制。我们所说的常识一般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常见的一个行业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是行业常识,一个专业领域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是专业常识。例如,吸毒导致成瘾是生活中的常识。美沙酮维持治疗主要适用于吸食或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这是禁毒领域的传统观点。常识范围的限制不仅仅体现在:这体现了价值在不同层面上的应用,也体现了知识的分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在司法判决中准确区分和适用不同范围的常识对于确保判决符合常识至关重要。 (2)常识的显而易见性和证伪性。一般来说,常识既有显而易见性,也有证伪性。常识的显而易见性源于人类感知经验的普遍性和即时性。 “扣除”授权或:陈家英版:华夏出版社,2011年5月“常识是指简单而基本的事实和原理,因此通常不需要证明或解释。常识意味着事情是这样的。”在内容从常识转变为常识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讨论和争议,以提炼其有效性。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常识为人们认识社会、遵循秩序提供了认知模式和规范基础。它是社会成员共享的认知框架。常识的明显性质使得这个过程既经济又方便。在社会交往中,常识作为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是提高公共推理理解、促进社会“有机统一”的实践智慧。从社会成员的行为来看,常识的显而易见性意味着它是自然的。l 让社会成员学习现有常识并遵循常识;即符合常识的行为是日常行为,社会成员自然会学习现有的常识并遵循常识;这意味着无需考虑合法性。因此,常识的显而易见性也与常识的直观反应密切相关。人们无法识别自己的常识,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无法判断自己行为背后的常识因素,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是因为人们通常不需要详细研究具体的常识机制,因此依赖于长期的常识认知。当这种无可争议的常识状态进入司法程序时,它就显得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需要论证或证据。然而,常识的显而易见性是建立在其可靠性的基础上的,总是存在异常和异常的情况。社会上的例外。 “常识出错的可能性实际上非常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化,还因为理解的局限性。”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虚拟技术和“元宇宙”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常识。在全球首例人工智能机器人导致死亡事件中,聊天机器人的指导言论对人们对人机关系的常识性理解产生了巨大影响。几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人们外出时应该非常小心,避免现金被盗。移动支付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因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的变化,形成新的常识来取代以前的常识。知识层面的常识可以成为经验和判断层面的常识。公共服务之间存在动态的沟通关系行业常识、专家常识、生活常识。一旦工业和专业常识广为人知,它就会成为日常生活常识。常识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削弱其显而易见性。这意味着关于某些内容的常识可能在某些时间或场景下变得可疑,人们在接受新信息时可能会感到困惑。篡改常识就是动摇原有的常识。电影《秋井的要求》(1992) 的剧照。常识系统内的其他细分决定了特定常识的反驳程度。如上所述,常识根据内容层次的不同,有不同形式的知识、判断和思维方式。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可驳斥性也有相应的差异。关于自然法则和众所周知的事实。毫无疑问我们的知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以不可抗力的情况来反驳。对于一些涉及肤浅常识生活经历的内容,一致的强度可能会因当事人的年龄、生活经历、所在地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老年农民比城市年轻人有更多的农业和气象知识。此外,中国北方人对丧葬义务的理解可能与其他地区的人不同,例如“站在锅上”和“打破锅”。判断意义上的常识与司法判断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可以限制或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其反驳对于司法判决更为重要。例如,在一起专业贪污案件中,对于被告是否处于有利地位,检方认为托运人封存货物即表明其仍处于控制之中。因此,开车的李先生被告人上海深航的总经理万先生在经营过程中无意挪用公款。但仲裁庭认为,从日常生活常识来看,用胶带密封纸箱仅用于包装产品,防止散落,并不能达到密封防盗的目的。李先生在履行职责期间对该资产拥有实际控制权,这符合其职务。在本案中,检察官的裁决是“封存物品意味着他们仍然拥有物品的控制权”,而法院的裁决是“封存物品是为了防止其分散,对于防止盗窃没有意义”。在此,控辩双方对查封财产的常识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对于判断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具有重要的启示。一般情况下,常识是它在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意识中保存得非常明显,而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则微乎其微。然而,在本案中,常识成为讨论话题,意味着当事人对基本内容存在不同看法,也体现了判断意义上对常识的反驳。关于观念和价值观层面对常识的驳斥,不言而喻,价值观的平衡始终是一个经典的司法问题。电视剧《底线》(2022)剧照。一般来说,常识内容的反驳与其所蕴含的共识的强弱密切相关。常识的“常态”代表了社会的基本共识,是不言而喻的,但常识的“常态”“知识”是凝聚了各个层面共识的知识集合,是其可证伪性的根源。意义不可能变得普遍意味着它的使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介绍了用常识推理的不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论义务。换句话说,常识的显而易见性赋予了它最初意义上的合法性。一旦法院判决出现争议,就必然需要证据来反驳。干预和揭露证据。 2、审判常识的运用 作为法官的一项重要规定,常识在审判中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当用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法律方法论来解释司法程序时,常识几乎在整个司法过程中都具有价值。例如,“每个民事法官都会遇到‘明显代表’裁决的问题……法官的常见做法有时是决定是否援引明显代表制度以及谁应该承担责任”法治问题:基本司法观察笔记 作者:赵耀通 版本:中国法律出版社 2020年12月 常识是普通民众解释正义和规范的重要依据,并鼓励法律规范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良性互动。如果我们将案件形成的过程简化为三段论推理,以案件事实为推理的小前提,法律规则适用于案件事实是大前提,最终判决是推理的结论,可见,常识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建构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没有必要区分适用常识的效果是体现在事实的形成过程中,还是体现在事实的形成过程中。论证事实的过程。 (一)常识作为无证据的事实《疑难案件的判断理论与方法:中国法理学的司法应用》作者:子林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9月“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常识对于判断案件事实的真伪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生活经验在认定事实中的作用和规则也将由法律明确规定。”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常识的事实判定可以在法律体系内固定和规范。这种常识通常是常识体系的表面内容,也是最客观的部分。立法者基于或相信这种常识的客观性,通过立法等程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呈现出其无可置疑的、不言而喻的特征,构成了现代司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麦克风系统。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解释[2022]11号)第九十三条规定了没有证据的事实,其中“自然规律、定理和规则”、“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规则推定的其他事实”都属于常识性质。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1条(高检发佛事字[2019]4号),将“为公众广泛知晓的常识事实”和“自然规律、法规”作为排除事实。这一司法承认规则是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承认的。除一般意义上的排除事实进行界定外,在具体案件中,法官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进一步限定排除事实的范围。例如,二审法官发现我国的医学研究人员以及公安、司法等相关部门的官员,对各种药物的成分、性质、滥用方法、症状以及对人体的危害等进行了全面、权威的研究,并通过书籍、网站、新闻等媒体,针对公众开展了广泛的禁毒宣传。因此,法院即使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也可以通过参考上述常识信息来判断吸食冰毒的症状。在关于智力虔诚的诉讼中,“常识”可以被用作排除的事实。常识是一种职业常识。由该领域的专家获得的特定领域的一般技术知识。它通常出现在该领域的教科书、专业词典、技术手册和其他参考书中。一些学者将这种类型的“伴随并基于共同的证据”称为“证据”。“常识”作为常识证据而不是科学证据。按照常理来说,通过司法认定作为无证据事实来呈现证据更为经济,但单靠司法认定一般无法完成对案件全部事实的认定,而常识的事实部分基本上仍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人们对事实的认识,这在客观性上与自然法不同。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事实内容并不完全客观,因此存在被用作无证据事实的可能性。毕竟,只要事实的客观程度不违反司法证明的要求,就可以作为未经证实的事实;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常识性事实能否作为无证据的事实存在争议,则应允许异议方出示证据,这一点值得注意。常识性的知识不应与先验知识或‘常识性概括’混为一谈。”常识事实本身可以作为未经证实的事实,但根据常识或其他生活经验推论而形成的事实当然不能作为未经证实的事实,特别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存在严格的证明标准。编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 (2) El Sentido común como base de la evaluación de la evidencia “¿Cómo puede un juez saber si alguna evidencia podría influir razonablemente en su evaluación de la probabilidad de la Existencia de un hecho putativo?… Por lo General, la respuesta debe dependenter de lapersonidad, experience, Sentido común y comprensión de las acciones y motivaciones de las personas”。” El artículo 139 de la “Interpretación del Tribunal Popremo sobre la aplica《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刑法释[2021]N.º1)规定,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审查人民检察院的基本情况。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以及证据之间的关系,往往需要运用常识来判断。证人证言,特别是当事人主观良心的判断,龙宗智教授曾经说过,普通人如果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必要的生活经验,就可以对证据进行判断,并且可以是合理的判断,包括合理的判断。奥布特。合理怀疑原则能够化繁为简。常识被用作评估证据的基础。它通常不是用来加强证据,而是用来排除与常识相矛盾的证据。这种情况被称为“常识问题”。 《刑事案件侦查流程研究:基于法官程序实践的视角》作者:李世峰编译:法制出版社在2020年7月的一起产权纠纷案中,某公司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在再审期间(2015年)提交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住宅租赁协议》。法院没有接受这一证据。法院根据常理认为,无论两家公司是否确实签订了“住宅租赁合同”,都应尽快将合同提交给涉案房屋的新业主。然而,直到该案重审之前,这件事已经四年没有被提及,并且合同中使用的注册印章与工商登记申请等场合使用的公司注册印章存在显着差异。本案判决摘要明确指出,当事人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证据是否可以作为证据,必须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拍卖过程、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举证时机等事实,并结合社会生活常识来认定。如果证据违反了自然法则的常识,那么它比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证据更有可能受到负面评价。例如,在非法采矿案中,检察官的实物检查笔录记录如下: 长江市民族吴村委会袁庄松沙坑,河沙45米南北长,高14米,东西长42米。这些记录的数据表明,沙山的形状是长方体,但根据当时拍摄的现场照片来看,沙山的形状并不是长方体。根据生活经验和物理知识,露天沉积的河沙形成的沙堆不太可能是长方体,特别是当长和宽超过40米时,其形状更不可能是标准的长方体。从程序实践的角度来看,运用常识评价证据时,常识不仅可以评价证据的证明力,还可以评价证据的证明力。证据符合常识是正常的。当证据不符合常识时,常识在质疑和拒绝证据中的作用就很重要。强调。 (3)常识作为事实推理的主要前提。复杂的案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时,可能需要利用有限的间接证据来推断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一百四十条对间接证据的推断作出了具体规定。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证据被确认属实。(二)证据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和莫名其妙的疑点。(三)整个案件的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四)根据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结论是:“(五)我使用共同的证据进行调查。你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 “对案件事实进行间接推理的过程,通常是从知识库中提取一些内容作为推理的大前提,并以证据事实作为小前提来完成推理过程。大前提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描述’,它是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如何运作、关于人类的行为和意图、关于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一般性陈述,在某些情况下,它们采取对人类行为和与其相关的客观问题进行更具体的总结评估的形式。一般描述的可靠性陈述可以从“无可争议的科学真理到基于专家意见的或多或少确定的形式”、“知识”,本质上是一般知识。法院认为,经验、信心、猜测、神话和偏见,其可靠性逐渐降低。永定河不是正常活动或通行的地方,与常识相比,危险后果的可预测性有助于确定某些地区的案件事实。法院认为,VIN,即车辆识别码,由17个字符和数字组成,是识别车辆的重要字符,而在我国,第10至17个字符是代表制造年份、制造工厂、生产线序列号等的字符串。车辆底盘号缺失,不影响车辆的识别。本案中,法院根据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必须具备的常识,推定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在于原则上,它为事实推理提供了一个基本起点。 “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不应该基于行为者或其伙伴的独特经历,而应该基于社会的共同经历,或者基于他们的相互理解。”常识作为一般性陈述或经验法则中最可能的部分,是其可靠性和普遍性的基本条件。然而,作为理性推论的一般陈述和作为例外事实的常识陈述之间存在差异。常识作为例外事实,其本身可以直接认定为示范性事实,但常识等一般性陈述的内容只能作为事实推论的基础。作为推论的小前提,推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来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解释》(法解释[2018]1号)规定,因客观原因不能确定当事人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官职业道德,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证据,逻辑思维、生活经验和常识,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在强拆房屋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不能证明房屋内物品丢失的,可以行政如果行政机关因未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和公证而无法证明房屋内物品丢失,则房屋的原状、当地居民及原告家庭的生活水平和习惯等都将成为常识推理的界限,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往往难以对索赔额进行判断。对远远超出当事人生活标准的贵重物品进行赔偿。现代司法中,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包括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以及实质性证据和佐证证据。常识事实推论通常基于间接或支持证据。这些证据构成了常识推理所必需的小前提,是常识推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识无法直接形成案件事实。电影《愤怒的男人》剧照(1957)。 (四)以常识为基础的判断作为纠正案件事实的基础论证的形成基于法律推理,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天然的差距。在法律推理中建立主要前提和次要前提之间的逻辑联系可能需要对法律规则的解释,或者根据既定规则对前述事实进行解释,完成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的逻辑适应,并对前述事实进行归属。在此过程中,常识可以作为考虑案件事实和结果的重要依据。例如,在教材中引用他人的作品而不明确提及是否违反了《版权法》中“适当引用”的规定?常识告诉我们,教材是随教科书一起提供的。即使被诉侵权作品中未明确标注作者姓名,读者仍须结合教材原文使用该书。教材原文中已明确注明作者信息,读者在使用前应考虑到这一点。因此,被诉侵权作品的相关行为不违反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此外,基于从教材的功能来看,被诉侵权作品不具有替代效应,将教师、学生等主要受众从侵权作品转移到被诉侵权作品上。相反,它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检察官指控被告在地下停车场发生的致命事件中存在疏忽。法院根据常识分析认为,驾驶员不可能预料到在仅供内部使用的地下车库内道路上会躺着行人,而且根据犯罪现场的地形位置,驾驶员在车辆下坡行驶时会存在一定的盲区。根据公众的看法,肇事者以他的能力和当时的情况无法预见所造成的损害。因此,本案中,不能严格归咎于被告人。e 损害。 “基于常识和生活经验对事实的认识,有时比基于法律程序的假设和判断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的正确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常识具有价值导向的重要性,司法部门必须通过特定的认知框架来评价人类的行为。作为司法知识的重要范畴,常识与“一般规则”、“良知”等概念共同建构着普通民众的司法立场,并构成了司法判决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理性面。常识符合老百姓标准不仅将评价引入司法程序,而且将不符合老百姓标准的评价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例如,如果两个孩子在溜冰场发生碰撞,那么争论到底应该归咎于年仅 6 岁的孩子还是肇事者,就没有任何常识或意义。损害的后果。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第40号判决孙立兴诉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局工伤事故认定案,针对园区劳动局的论点,法院认为,排除从工作场所完成工作的合理路线,违背了法律的初衷和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即使对某一特定事实的描述或评价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支持,但只要有常识的人认识到这一事实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这一事实或关系就可以产生法律权利和义务,并需要常识作为考虑后果的基础。电视剧《大宋的惩罚者》(2005)剧照。价值观层面的常识决定法官必须不断地审查自己的判决,决不能我们忘记了他们作为社会普通成员所需要的意识。 “它违背了常识;无论是作为理性问题的常识还是作为物理问题的常识,它都违背了道德的要求”。显然,律师用高度专业化的理念来形成独立世界中的正义,或者出于正义代言人的优越感而无视普通民众的常识判断,无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相反,当常识被用作不容置疑的判断而其背后的真正决策被有意或无意地隐藏时,情况就更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程序中应用常识的主要目标陪审团制度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推崇,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行,基于司法审判评估普通民众的常识和价值判断的需要。在调查过程中,陪审团可以做出贡献非职业法人的常识,调整以法官为代表的职业精英的知识和价值观。然而,陪审团制度所面临的陪审团与职业法官之间权力划分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常识与规范权威之间的复杂关系。三、司法审判中运用常识的条件 常识在几乎所有的司法量刑过程中都发挥着作用,但某一内容是否可以称为常识、司法机关如何评价该常识内容、司法机关如何根据常识作出判决,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不同水平的常识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随着每个案件具体情况所设定的具体情景,司法判决的常识含义也有所不同。因此,法官不仅要审查常识本身,还要对常识与待决案件的兼容性做出必要的判断。这些内容是常识适用的条件,也意味着常识的适用是有限制的。 (一)常识内容的规范性必须满足司法裁判的规范性需要。所谓规范性,是指为人们建立行为标准。我们不是解释人们的行为,而是告诉他们他们有权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事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不能直接影响审判的结果。这类常识与法律规范具有协同作用,为司法判决提供了互补的理解。 《合法性》 作者:[美]斯科特·夏皮罗 译者:郑玉双、刘业胜 版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年12月6 例如,当我们说7日晚上发生某事时,这里的“夜”一般指“从黑暗到黎明的时间”。这意味着这一晚包括7日晚上和8日凌晨,在法律上相当于2个日历日。在司法过程中,真正影响判决结果的是常识,包括从社会生活经验中获得的规范指导。例如,人们对合同的常识包括这样的理解:合同必须由至少两个当事人签署,并且合同各方都必须履行。有学者将这类常识称为“规范事实常识”或“制度事实常识”。 《论法律作为常识的制度化》作者:叶一洲版:中国法律出版社2020年6月当我们认定某物为“合同”时,它不仅仅包括对与合同相关的规则和制度的基本了解。还包括人们对应该遵守上述规则的判断。如今,常识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维持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当一方声称某件事是“常识”时,通常意味着人们应该遵守支持它的规则。关于人际关系和行为内容的常识是否符合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尤其是是否不存在隐性偏见和歧视,需要进一步明确。从个体角度来看,人们对常识的获取可以通过系统的知识学习来实现,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经验、自我反思、文化传承中归纳得出结论。它是自发地、自然地形成的。经验意义上的常识是常用的盟友可靠,但并不总是如此。人们的头脑中可能存在伪装成经验常识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以常识之名参与司法程序,本身并不构成常识,即使构成也可以理解为常识,但其规范程度并不能为司法判决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认知贡献。因此,当当事人提出一定程度的常识作为主张的依据时,法官需要做出规范性的判断来回应。例如,在张某与卢某(夫妻)被指控共同诈骗的案件中,卢某的律师辩称,卢某的行为是由其丈夫张某指使的,张某并不知道张某是否有诈骗其粮款的意图,而她按照张某的指示进行的行为符合中国家庭道德和常识经验。这里的经验常识既不是自然法则,也不是原则或原则社会认可的意识。充其量只是当事人的经历和社会的认识。这不符合常识,更不符合司法决策的规范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接受法律体系的价值判断,即使内容被认为是“常识”。比如,在补偿方案中,我国部分地区因房屋征收和移民安置,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受到与男性不同的待遇。虽然这种做法确实可能构成特定群体或地区内部的“经验共识”,但其中存在的歧视性因素与法律秩序相矛盾。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常识引入司法程序。 (二)要使常识的“常态”适应判断的“差异”。学者们发现,法律实践中“常识”裁决的出现有两个前提条件冰。首先,与具体司法或执法实践关系较远;其次,关于具体司法或执法实践的信息不多。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解释这两个条件。在priFirst中,常识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遥远的,这意味着常识本身通常不是案件的重要事实。在欺诈案中,被告声称某些宝石具有神奇的特性和价值。常识表明,被告声称的魔法石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这部分被排除在证据之外。但无论被告是否构成诈骗罪,更重要的是判断被告是否捏造事实、非法占有财物,骗取他人欠款。其次,本案缺乏充分的直接证据,现行法律规定给常识的适用留下了空间。 F又比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结合刑事措施来判断被告人应对死亡后果的主观状态。这是因为他的基本常识被浓缩成犯罪工具。刀具、枪械等立即致死、逐渐致死的毒药等,可能反映了被告人对伤害程度的预期。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被告人使用的鱼叉或砍刀与受害人的多处撕裂伤或穿透伤相符,就可以明确判定主观故意。在这些案件中,鱼叉、砍刀以及受害者的多处割伤和穿透伤都是重要的证据。法官结合常识和这些重要的测试来推断犯罪的主观意图。当直接证据确凿,或者常识的内容与案件的重要事实一致时,常识的作用就不那么突出了。推论结果与社会普遍认知一致。 “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这是生活中的常识,通常很难对案件的侦查做出多大贡献。在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声称因过量饮酒导致死亡是因意外伤害,因此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法院认为,过量饮酒有害健康是生活常识。法院认为,饮酒行为本身不满足意外伤害所包含的外在的、突发的、非自愿的因素,认定其不构成意外伤害。本案常识内容的普遍性已达到与案件事实的特殊性相适应的状态。正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饮酒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酒精的影响也随之而来。赔偿应当在当事人的意识范围内,事故造成的伤害之间的界限应当明确。判断常识与待决案件是否相容,关键在于常识的内容是否有助于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内直接回应具体案件的事实争议。例如,日本《汽车事故责任保险条例》规定了酒后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这样的常识在解决责任纠纷中没有立足之地。在抢劫案中,法院发现,侦查机构根据齐木林辨认的尸体倾倒地点进行了调查实验,辩方也根据齐木林辨认的地点分析了尸体的漂移轨迹。根据扶余市气象厅的分析,该物体废弃于富春江东武大桥南岸,特别是南岸附近。废弃物品可能滞留在桥附近的南岸。这个分析符合常识。法院采纳日本气象厅的意见可以理解,但日本气象厅的分析是专业意见,常识是一般认识。仅通过与常识进行比较,无法确定日本气象厅的分析是否可以被采纳。此外,法院在此并未确认任何常识。换句话说,用常识来解释日本气象厅专家意见的可接受性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众所周知,在道路交通领域,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距离是强制性的,也是驾驶时的常识。这一要求主要是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通常包括这样的先决条件:您的一方不会对他人的驾驶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前述青岛行人碰撞事件中,案发现场视频显示,两名行人均未注意观察,均做出严重影响他人的动作,且未包含驾驶场景。我们看到,法官所表达的常识性陈述与证据和事实不符。审判中可能存在多个事实问题,可以使用常识来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这一事实争议是一个重要事实。即使没有这样的事情,常识和司法判例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可以共存的。有专业人士指出,常识性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且是片断的。与构成犯罪的证据相比,它在案件的证据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非中心位置。仅凭常识证据几乎不可能证明案件事实。电影《Article 20》(2024 年)剧照。在强奸案中,上诉人辩称,性关系是双方自愿的,不构成强奸。法院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监控录像包括:视频数据、检查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确认。法院还认定受害人的性取向为女同性恋,并认定辩方的“武断”意见无法明确表达,有悖常理、常理和传统智慧,因此无法成立。本案中,涉案证据构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完整证据链,并以围绕“受害人是女同性恋”形成的常识性判断作为实质性和全面性的依据。强化证据有效性。综上所述,常识的“恒常性”决定了它只是某些社会关系的共同内容,而每一个案都是特殊的。常识通常与特定案例中必须证明的事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司法机关只有明确常识与需要证明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适用常识。 (三)违背常识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讨论。在司法程序中,当遇到普通的分歧和争议时,换句话说,有理有据的论据通常被认为比无理据的结论更可靠。这至少会要求法官相信这些说法,也会减少他们在未来案件中做出决定的自由。在司法程序之外,辩论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听众的尊重,可以凝聚更广泛的共识,增强司法公正。红色性。司法诉讼争论根本上需要解决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特殊关系。无论是法律的适用还是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都必须提供理由或理由来支持其结论。这已成为共识。刘星教授曾说过,在日常生活中,用“经验和常识”去尝试事情是很困难的。他指出,法律程序可能会很困难。其根源在于,法律辩论比日常生活中的辩论更能揭示利益和是非立场的复杂性。法庭诉讼中讨论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比日常生活中受到更多的审视、期望和要求。司法逻辑:实践中的方法与正义 作者:刘星 版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5 年 11 月 如上所述,常识的明显性质为司法程序中常识的运用提供了初步的合法性。如果司法程序的各方及其潜在的支持者都不质疑常识的内容及其适用,那么此时就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正如常识的内容存在差异一样,常识的显而易见程度也存在差异。运用常识并不能完全免除司法机关的抗辩义务。当常识的应用受到质疑时,需要进行合理的辩论。一些学者指出,“只要基于‘常识’,即非专家的理性推理和常识,对判决的审查就是自由的”。这句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意味着常识是衡量法官举证责任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人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判断常识的储备情况审判中的人和受众也不同。当司法程序中出现常识性分歧时,辩论是必要的。诉状的直接目的是通过诉状回答当事人的常识性问题,达到司法判决的目的,凝聚法律界的共识。尽管常识在司法判决中的运用并不一定是核心;一旦司法判决偏离常识,就会对公众对正义的稳定预期产生强烈影响。因此,法官也必须关注公众的反应。与专门的法律判断相比,常识性问题没有专业障碍,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争论。法官在针对公众的辩论中使用的资源和辩论策略也应该不同于针对专门话题的辩论。最有效的论证策略是用一种常识来解释另一种看似荒谬的事实,即将不寻常的事情归咎于另一种常识。如果法官的判决违背常理,即使法官对他的判决感到满意,l的论证负担也会很低。らに重くなる。在抢劫案中,被告称自己去早市买了红针。法官指出,红枪鱼生长的最佳温度是20至26摄氏度。案发时间3月13日上午8点左右,由于气温不适合马林鱼生长,没有人出售马林鱼。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不过,红马林鱼是观赏鱼,而非食用鱼,一般大众对其适宜的生长温度了解不多。只有经常养鱼的人或者专业养鱼的人才会明白这一点。当法官将这种不太普遍的知识称为“常识”时,需要进一步了解解释是不可避免的。电视连续剧《胜利者是对的》(2012) 的框架。在一场外观设计专利纠纷中,一家公司认为其外观设计专利受到侵犯。外观设计为一款手持花洒产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普通消费者的知识和认知能力,淋浴喷头产品必须包括淋浴喷头和手柄两个主要部分。这两种设计特征在使用过程中易于直接观察到,构成了花洒产品整体视觉效果的基础,赋予了产品设计美感。因此,认定两种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存在显着差异,不构成相似。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按钮虽然可以有多种形状,但其在手柄上的位置主要是基于功能设计,不会明显影响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新审判决h众所周知,吸嘴、手柄及其连接部件是容易被普通消费者看到的部件。按钮的作用是控制水流开关。普通消费者在看到花洒手柄上的按钮时,不仅会考虑该按钮能否起到控制水流开关的功能,自然也会关注其装饰性,考虑按钮的设计是否美观。在本案中,三级法院从普通消费者的经历出发,但结论和推理却有所不同。其中,二审裁决受到当事人质疑,称其“有悖常理”。确定哪些决策“违背常识”需要仔细讨论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此案在三级法院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虽然不能说结论的唯一正确性是在绝对意义上得到了证实,如果我们反思前两次审判的句子,新审判的句子中通过论证过程表达的常识判断显然更可靠。剩下的观察:常识的辅助地位和理性的运用。常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认知系统。常识是社会经验的结晶,内容极为丰富,对司法程序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常识的运用必须继续辅助事实的调查。根据具体情况,常识的作用必须与证据结合起来。 《明清民事审判与民事合同》 编者:王亚新、梁志平、赵静 编者:禾木出版社,2022年5月 当事实分为直接客观事实和背景事实时,在司法审判中,基于常识对事实的调查往往会被忽视。功能作为背景事实。即使常识作为排除事实,一般也不构成案件的重要事实。在另一些情况下,常识作为评价证据和推断事实的基础,其主要作用是促进证据事实转化为最终的判断事实。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识无法完成认定案件事实的任务。在个人层面,基于常识的判断通常以直觉的形式出现。这种综合直觉的机制极其复杂,包括法官在内的直觉主体并不一定能准确把握这种直觉的本质和正确性。因此,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适用,其可靠性都不是基于个人的常识直觉。法律、证据和相应的规则构成实质性常识判断的局限性。从司法论证的角度来看,司法裁判解决纠纷的目的是特殊的、具体的。由于常识的普遍性和普遍性,它主要作为论证中的基本一致,但很难将其用作客观一致。在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常识的作用更加有限,有些案件的事实必须通过专业评估等特殊程序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律和常识无法得出结论时,司法机关只能选择接受技术权威的意见。专业化程度越高,常识的作用就越有限。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已经走得太远了。”经验压力下,司法实践中出现另一种趋势:司法机关过于依赖身份核实等专业判断,抛弃常识性判断意见和“常识判断的功能逐渐弱化”。电影《证人》(2013)剧照。现代技术与常识之间的复杂关系相互促进、相互竞争,但常识的边界在不断转移,专业判断与常识推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如果司法过度依赖技术权威,忽视常识的普遍性,法院的社会认可度就会下降,可能导致“司法贫困”的困境。传统常识司法意见的不断出现,进一步强调了在个案中准确运用常识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常识的运用必须积极、谨慎,保持规范考虑、案例适应和讨论必要性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在涉及的情况下在价值观冲突的情况下,常识应该服务于法律体系的总体目标,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按照之前的顺序。当然,常识对于正义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常识理性始终为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常识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不仅为行为提供了基本准则,而且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朴素智慧、信仰和意识。在常识、法律规范和技术权威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常识允许我们识别和区分基本社会信仰和个人偏好及任意假设,避免司法决策出现不合理的偏差。常识的合理性总是邀请我们进行实际反思。在复杂的社会概念中,“我们分享什么,我们应该分享什么”这是常识对于司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常识和理性的基础上,司法机构、法律工作者群体和公众之间才能建立信任和良性互动。法律只有植根于日常生活,才能保护人们日常生活中珍视的价值和意义。【来源】吴非:《论常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第172-183、192页。 作者:吴飞(山东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 此事点评:陈
“随着现代技术和常识的进步并在复杂的关系中竞争,常识的界限正在不断变化。” ——吴非:《论常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第172-183页,第192页。本期审阅:陈新宇黄殿林文字摘录:罗东在现代,除了书籍之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另一个基本手段。今年8月以来,《京报书评周刊》拓展了以书评为基础的“学术评论与摘要”的知识传播工作,并筹办了“京报中文学术摘要服务”,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杂志界和《人大报纸资料复印》、《社会科学摘要》等摘要刊物提供服务。每周出版一期,每期推荐两篇文章。每期均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最新、专业、前沿的文章。我们也希望入选的文章具有清晰的本土和全球问题意识,具有独特的中文写作气质。这是第九次了。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吴飞分析了常识与司法判决的关系。根据常识的理解,常识是常识,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或某一特定专业内的大多数专业人士)认可的不言自明的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案件的处理结果明显违背一定程度的常识时,通常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民群众对正义的期望。常识是社会的基础。除了支持司法判决外,还有o 对其使用的限制。笔者以辩证的态度、谨慎的态度来分析两者的关系。以下内容经社会科学许可转载。请参阅原始出版物的摘要、表格、参考文献和注释。作者 |剧照来自吴非的电视剧《以法律之名》(2025)。常识作为日常社会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了基本认识,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化程度。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常识构成了人们在社会经验问题上趋于达成共识的重要认知基础,是主体间性的关键要素。在司法领域,常识也构成公众对司法稳定期望的认知基础和心理。司法判决必须始终符合常识。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判决结果仍然与事实相矛盾。符合常识或明显偏离常识。此前,鄂尔多斯“贵毛衣事件”和天津赵华非法持有武器事件曾引发争议。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在一起行人碰撞案件纠纷中使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表述,引发广泛质疑。法院随后发布了现场视频并道歉以平息争议。学者们将这种特殊情况称为“反常识”或“后常识”现象。从案件判决的整体社会影响来看,“有悖常理”现象的出现,强烈影响了司法预期的稳定性。学者们针对这些类型的问题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在此过程中,他们卓有成效地探讨了如何避免常识的认知偏差,并就常识的作用和重要价值达成了共识。司法决策中的nse。需要注意的是,案件违反常识并不一定意味着法院判决本身就是错误的。从其规范性来看,常识作为知识体系是基础性的、普遍性的,而对具体案件的调查则必须是具体的、具体的。两者之间永远存在天然的差距。再者,每个人都有常识,但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培养。它可以改变。因此,当出现共识问题时,单方面批评司法判决可能过于短视。本文旨在强调常识与司法判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常识,增加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具体来说,如果常识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它是否可以在司法程序中受到质疑和审查?不同级别的c如何常识有利于司法判决规范的形成吗?在司法判决中运用常识的条件和限制是什么?但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和研究。一、常识的内容层次和基本性质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将其与常识、常理一起使用,但其含义与“理”的概念几乎相同。相比于常识和常识的语境依赖,常识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恒定性,其稳定司法预期的作用更加明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常识很容易适用于司法实践;有些常识是基于人们的经验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些常识却是有争议的,这使得法院案件的处理更加复杂化,并引发了常识之争。常识的这些复杂属性源自其具体内容。因此,深探讨常识的内容层次和基本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常识在司法裁判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性。 (一)常识的内容层面 常识作为一个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中国经典中有一个词叫“common sense.n”,基本意思是日常知识。现代意义上的“common sense”一词一般认为是日本明治时期创造的新词,19世纪末传入中国并吸收到汉语中。根据《汉语词典》的定义,common sense是指一般知识。汉语中使用的“一般生活经验”、“一般规则”、“公序良俗”等概念中也包含常识。常识的概念是commonsense,源自sensuscommunis,指的是主要以感觉为基础的共同情感和意识。到了现代,它已经成为一个指代人类认知能力的概念,其含义几乎等同于智慧、智慧、理性和实用主义。陈家英教授认为,中文的“common sense”重在表面的事实,而英文的“common sense”重在事实中蕴含的真理。常识通常与对非凡事实和深刻真理的理解有关,特别是与理论知识和理论体系有关。 《比较法视角下的证据制度》 作者:【美国】Mirjan R. Damaska 译者:吴红耀、韦晓才等版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常识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取决于其内容被学习、加工和内化的程度。第一层次也是肤浅的层次,其中知识,尤其是事实,表现为关于某事物的一些知识。他们来自p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历,属于“经验知识”。第二个层次的常识是基于上述知识总结出来的一系列原理和判断。这些判断是基于对事实的一般和共同理解。如果判断的专业性和深刻性很高,那么它就不属于常识的范畴。第三个层次可以理解为在常识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意识”的含义由此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识为社会个体成员与外界之间的精神沟通和价值认同提供了条件。当然,这个常识水平是相对的。 “当谈到人类生活的事实时,很难有简单的事实。事实和社会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生活的事实最初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创造的。” 《论可能的生活》作者:Zh敖汀阳版:生活/阅读/新知 三联书店2024年9月 社会人们普遍理解和认可的道理,是在掌握基本常识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有些已经属于常识的判断本身就是常识。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用词来看,司法文书中通常不区分常识和常识含义。然而,当用于评估行为时,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异。常识侧重于从理性的角度评价人们的行为,而常识则侧重于从认知的角度评价人们的行为。常识评估更为基础。一般来说,表层常识构成了人们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而判断意义上的常识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调节作用则更为突出。常识为人们建立基本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说,人们不仅遵守常识,而且也期望别人遵守常识。换句话说,违反常识就被认为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深刻的常识,即思想意识和良心意识的常识,是评价司法判决整体价值的指南。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是由特定社会所接受的一套信念组成的,并且该社会的成员假设这些信念是所有理性人所共有的。这些不同层次的知识和原则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智慧,是公众形成的最普遍的经验,也是所有文化中最共同、稳定、流行的要素。除了内容的层次之外,常识的范围也受到限制。我们所说的常识一般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常见的一个行业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是行业常识,一个专业领域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是专业常识。例如,吸毒导致成瘾是生活中的常识。美沙酮维持治疗主要适用于吸食或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这是禁毒领域的传统观点。常识范围的限制不仅仅体现在:这体现了价值在不同层面上的应用,也体现了知识的分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在司法判决中准确区分和适用不同范围的常识对于确保判决符合常识至关重要。 (2)常识的显而易见性和证伪性。一般来说,常识既有显而易见性,也有证伪性。常识的显而易见性源于人类感知经验的普遍性和即时性。 “扣除”授权或:陈家英版:华夏出版社,2011年5月“常识是指简单而基本的事实和原理,因此通常不需要证明或解释。常识意味着事情是这样的。”在内容从常识转变为常识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讨论和争议,以提炼其有效性。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常识为人们认识社会、遵循秩序提供了认知模式和规范基础。它是社会成员共享的认知框架。常识的明显性质使得这个过程既经济又方便。在社会交往中,常识作为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是提高公共推理理解、促进社会“有机统一”的实践智慧。从社会成员的行为来看,常识的显而易见性意味着它是自然的。l 让社会成员学习现有常识并遵循常识;即符合常识的行为是日常行为,社会成员自然会学习现有的常识并遵循常识;这意味着无需考虑合法性。因此,常识的显而易见性也与常识的直观反应密切相关。人们无法识别自己的常识,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无法判断自己行为背后的常识因素,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是因为人们通常不需要详细研究具体的常识机制,因此依赖于长期的常识认知。当这种无可争议的常识状态进入司法程序时,它就显得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需要论证或证据。然而,常识的显而易见性是建立在其可靠性的基础上的,总是存在异常和异常的情况。社会上的例外。 “常识出错的可能性实际上非常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化,还因为理解的局限性。”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虚拟技术和“元宇宙”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常识。在全球首例人工智能机器人导致死亡事件中,聊天机器人的指导言论对人们对人机关系的常识性理解产生了巨大影响。几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人们外出时应该非常小心,避免现金被盗。移动支付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因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的变化,形成新的常识来取代以前的常识。知识层面的常识可以成为经验和判断层面的常识。公共服务之间存在动态的沟通关系行业常识、专家常识、生活常识。一旦工业和专业常识广为人知,它就会成为日常生活常识。常识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削弱其显而易见性。这意味着关于某些内容的常识可能在某些时间或场景下变得可疑,人们在接受新信息时可能会感到困惑。篡改常识就是动摇原有的常识。电影《秋井的要求》(1992) 的剧照。常识系统内的其他细分决定了特定常识的反驳程度。如上所述,常识根据内容层次的不同,有不同形式的知识、判断和思维方式。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可驳斥性也有相应的差异。关于自然法则和众所周知的事实。毫无疑问我们的知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以不可抗力的情况来反驳。对于一些涉及肤浅常识生活经历的内容,一致的强度可能会因当事人的年龄、生活经历、所在地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老年农民比城市年轻人有更多的农业和气象知识。此外,中国北方人对丧葬义务的理解可能与其他地区的人不同,例如“站在锅上”和“打破锅”。判断意义上的常识与司法判断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可以限制或规范人们行为的规范。其反驳对于司法判决更为重要。例如,在一起专业贪污案件中,对于被告是否处于有利地位,检方认为托运人封存货物即表明其仍处于控制之中。因此,开车的李先生被告人上海深航的总经理万先生在经营过程中无意挪用公款。但仲裁庭认为,从日常生活常识来看,用胶带密封纸箱仅用于包装产品,防止散落,并不能达到密封防盗的目的。李先生在履行职责期间对该资产拥有实际控制权,这符合其职务。在本案中,检察官的裁决是“封存物品意味着他们仍然拥有物品的控制权”,而法院的裁决是“封存物品是为了防止其分散,对于防止盗窃没有意义”。在此,控辩双方对查封财产的常识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对于判断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具有重要的启示。一般情况下,常识是它在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意识中保存得非常明显,而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影响则微乎其微。然而,在本案中,常识成为讨论话题,意味着当事人对基本内容存在不同看法,也体现了判断意义上对常识的反驳。关于观念和价值观层面对常识的驳斥,不言而喻,价值观的平衡始终是一个经典的司法问题。电视剧《底线》(2022)剧照。一般来说,常识内容的反驳与其所蕴含的共识的强弱密切相关。常识的“常态”代表了社会的基本共识,是不言而喻的,但常识的“常态”“知识”是凝聚了各个层面共识的知识集合,是其可证伪性的根源。意义不可能变得普遍意味着它的使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介绍了用常识推理的不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论义务。换句话说,常识的显而易见性赋予了它最初意义上的合法性。一旦法院判决出现争议,就必然需要证据来反驳。干预和揭露证据。 2、审判常识的运用 作为法官的一项重要规定,常识在审判中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当用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法律方法论来解释司法程序时,常识几乎在整个司法过程中都具有价值。例如,“每个民事法官都会遇到‘明显代表’裁决的问题……法官的常见做法有时是决定是否援引明显代表制度以及谁应该承担责任”法治问题:基本司法观察笔记 作者:赵耀通 版本:中国法律出版社 2020年12月 常识是普通民众解释正义和规范的重要依据,并鼓励法律规范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良性互动。如果我们将案件形成的过程简化为三段论推理,以案件事实为推理的小前提,法律规则适用于案件事实是大前提,最终判决是推理的结论,可见,常识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建构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没有必要区分适用常识的效果是体现在事实的形成过程中,还是体现在事实的形成过程中。论证事实的过程。 (一)常识作为无证据的事实《疑难案件的判断理论与方法:中国法理学的司法应用》作者:子林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9月“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常识对于判断案件事实的真伪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生活经验在认定事实中的作用和规则也将由法律明确规定。”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常识的事实判定可以在法律体系内固定和规范。这种常识通常是常识体系的表面内容,也是最客观的部分。立法者基于或相信这种常识的客观性,通过立法等程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呈现出其无可置疑的、不言而喻的特征,构成了现代司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麦克风系统。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解释[2022]11号)第九十三条规定了没有证据的事实,其中“自然规律、定理和规则”、“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经验规则推定的其他事实”都属于常识性质。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1条(高检发佛事字[2019]4号),将“为公众广泛知晓的常识事实”和“自然规律、法规”作为排除事实。这一司法承认规则是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承认的。除一般意义上的排除事实进行界定外,在具体案件中,法官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进一步限定排除事实的范围。例如,二审法官发现我国的医学研究人员以及公安、司法等相关部门的官员,对各种药物的成分、性质、滥用方法、症状以及对人体的危害等进行了全面、权威的研究,并通过书籍、网站、新闻等媒体,针对公众开展了广泛的禁毒宣传。因此,法院即使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也可以通过参考上述常识信息来判断吸食冰毒的症状。在关于智力虔诚的诉讼中,“常识”可以被用作排除的事实。常识是一种职业常识。由该领域的专家获得的特定领域的一般技术知识。它通常出现在该领域的教科书、专业词典、技术手册和其他参考书中。一些学者将这种类型的“伴随并基于共同的证据”称为“证据”。“常识”作为常识证据而不是科学证据。按照常理来说,通过司法认定作为无证据事实来呈现证据更为经济,但单靠司法认定一般无法完成对案件全部事实的认定,而常识的事实部分基本上仍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人们对事实的认识,这在客观性上与自然法不同。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事实内容并不完全客观,因此存在被用作无证据事实的可能性。毕竟,只要事实的客观程度不违反司法证明的要求,就可以作为未经证实的事实;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常识性事实能否作为无证据的事实存在争议,则应允许异议方出示证据,这一点值得注意。常识性的知识不应与先验知识或‘常识性概括’混为一谈。”常识事实本身可以作为未经证实的事实,但根据常识或其他生活经验推论而形成的事实当然不能作为未经证实的事实,特别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存在严格的证明标准。编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 (2) El Sentido común como base de la evaluación de la evidencia “¿Cómo puede un juez saber si alguna evidencia podría influir razonablemente en su evaluación de la probabilidad de la Existencia de un hecho putativo?… Por lo General, la respuesta debe dependenter de lapersonidad, experience, Sentido común y comprensión de las acciones y motivaciones de las personas”。” El artículo 139 de la “Interpretación del Tribunal Popremo sobre la aplica《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刑法释[2021]N.º1)规定,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审查人民检察院的基本情况。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以及证据之间的关系,往往需要运用常识来判断。证人证言,特别是当事人主观良心的判断,龙宗智教授曾经说过,普通人如果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必要的生活经验,就可以对证据进行判断,并且可以是合理的判断,包括合理的判断。奥布特。合理怀疑原则能够化繁为简。常识被用作评估证据的基础。它通常不是用来加强证据,而是用来排除与常识相矛盾的证据。这种情况被称为“常识问题”。 《刑事案件侦查流程研究:基于法官程序实践的视角》作者:李世峰编译:法制出版社在2020年7月的一起产权纠纷案中,某公司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在再审期间(2015年)提交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住宅租赁协议》。法院没有接受这一证据。法院根据常理认为,无论两家公司是否确实签订了“住宅租赁合同”,都应尽快将合同提交给涉案房屋的新业主。然而,直到该案重审之前,这件事已经四年没有被提及,并且合同中使用的注册印章与工商登记申请等场合使用的公司注册印章存在显着差异。本案判决摘要明确指出,当事人提交的“房屋租赁协议”证据是否可以作为证据,必须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拍卖过程、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举证时机等事实,并结合社会生活常识来认定。如果证据违反了自然法则的常识,那么它比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证据更有可能受到负面评价。例如,在非法采矿案中,检察官的实物检查笔录记录如下: 长江市民族吴村委会袁庄松沙坑,河沙45米南北长,高14米,东西长42米。这些记录的数据表明,沙山的形状是长方体,但根据当时拍摄的现场照片来看,沙山的形状并不是长方体。根据生活经验和物理知识,露天沉积的河沙形成的沙堆不太可能是长方体,特别是当长和宽超过40米时,其形状更不可能是标准的长方体。从程序实践的角度来看,运用常识评价证据时,常识不仅可以评价证据的证明力,还可以评价证据的证明力。证据符合常识是正常的。当证据不符合常识时,常识在质疑和拒绝证据中的作用就很重要。强调。 (3)常识作为事实推理的主要前提。复杂的案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时,可能需要利用有限的间接证据来推断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一百四十条对间接证据的推断作出了具体规定。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证据被确认属实。(二)证据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和莫名其妙的疑点。(三)整个案件的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四)根据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结论是:“(五)我使用共同的证据进行调查。你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 “对案件事实进行间接推理的过程,通常是从知识库中提取一些内容作为推理的大前提,并以证据事实作为小前提来完成推理过程。大前提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描述’,它是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如何运作、关于人类的行为和意图、关于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一般性陈述,在某些情况下,它们采取对人类行为和与其相关的客观问题进行更具体的总结评估的形式。一般描述的可靠性陈述可以从“无可争议的科学真理到基于专家意见的或多或少确定的形式”、“知识”,本质上是一般知识。法院认为,经验、信心、猜测、神话和偏见,其可靠性逐渐降低。永定河不是正常活动或通行的地方,与常识相比,危险后果的可预测性有助于确定某些地区的案件事实。法院认为,VIN,即车辆识别码,由17个字符和数字组成,是识别车辆的重要字符,而在我国,第10至17个字符是代表制造年份、制造工厂、生产线序列号等的字符串。车辆底盘号缺失,不影响车辆的识别。本案中,法院根据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必须具备的常识,推定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在于原则上,它为事实推理提供了一个基本起点。 “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不应该基于行为者或其伙伴的独特经历,而应该基于社会的共同经历,或者基于他们的相互理解。”常识作为一般性陈述或经验法则中最可能的部分,是其可靠性和普遍性的基本条件。然而,作为理性推论的一般陈述和作为例外事实的常识陈述之间存在差异。常识作为例外事实,其本身可以直接认定为示范性事实,但常识等一般性陈述的内容只能作为事实推论的基础。作为推论的小前提,推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来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解释》(法解释[2018]1号)规定,因客观原因不能确定当事人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官职业道德,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证据,逻辑思维、生活经验和常识,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在强拆房屋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不能证明房屋内物品丢失的,可以行政如果行政机关因未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和公证而无法证明房屋内物品丢失,则房屋的原状、当地居民及原告家庭的生活水平和习惯等都将成为常识推理的界限,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往往难以对索赔额进行判断。对远远超出当事人生活标准的贵重物品进行赔偿。现代司法中,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包括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以及实质性证据和佐证证据。常识事实推论通常基于间接或支持证据。这些证据构成了常识推理所必需的小前提,是常识推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识无法直接形成案件事实。电影《愤怒的男人》剧照(1957)。 (四)以常识为基础的判断作为纠正案件事实的基础论证的形成基于法律推理,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天然的差距。在法律推理中建立主要前提和次要前提之间的逻辑联系可能需要对法律规则的解释,或者根据既定规则对前述事实进行解释,完成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的逻辑适应,并对前述事实进行归属。在此过程中,常识可以作为考虑案件事实和结果的重要依据。例如,在教材中引用他人的作品而不明确提及是否违反了《版权法》中“适当引用”的规定?常识告诉我们,教材是随教科书一起提供的。即使被诉侵权作品中未明确标注作者姓名,读者仍须结合教材原文使用该书。教材原文中已明确注明作者信息,读者在使用前应考虑到这一点。因此,被诉侵权作品的相关行为不违反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此外,基于从教材的功能来看,被诉侵权作品不具有替代效应,将教师、学生等主要受众从侵权作品转移到被诉侵权作品上。相反,它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检察官指控被告在地下停车场发生的致命事件中存在疏忽。法院根据常识分析认为,驾驶员不可能预料到在仅供内部使用的地下车库内道路上会躺着行人,而且根据犯罪现场的地形位置,驾驶员在车辆下坡行驶时会存在一定的盲区。根据公众的看法,肇事者以他的能力和当时的情况无法预见所造成的损害。因此,本案中,不能严格归咎于被告人。e 损害。 “基于常识和生活经验对事实的认识,有时比基于法律程序的假设和判断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的正确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常识具有价值导向的重要性,司法部门必须通过特定的认知框架来评价人类的行为。作为司法知识的重要范畴,常识与“一般规则”、“良知”等概念共同建构着普通民众的司法立场,并构成了司法判决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理性面。常识符合老百姓标准不仅将评价引入司法程序,而且将不符合老百姓标准的评价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例如,如果两个孩子在溜冰场发生碰撞,那么争论到底应该归咎于年仅 6 岁的孩子还是肇事者,就没有任何常识或意义。损害的后果。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第40号判决孙立兴诉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局工伤事故认定案,针对园区劳动局的论点,法院认为,排除从工作场所完成工作的合理路线,违背了法律的初衷和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即使对某一特定事实的描述或评价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支持,但只要有常识的人认识到这一事实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这一事实或关系就可以产生法律权利和义务,并需要常识作为考虑后果的基础。电视剧《大宋的惩罚者》(2005)剧照。价值观层面的常识决定法官必须不断地审查自己的判决,决不能我们忘记了他们作为社会普通成员所需要的意识。 “它违背了常识;无论是作为理性问题的常识还是作为物理问题的常识,它都违背了道德的要求”。显然,律师用高度专业化的理念来形成独立世界中的正义,或者出于正义代言人的优越感而无视普通民众的常识判断,无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相反,当常识被用作不容置疑的判断而其背后的真正决策被有意或无意地隐藏时,情况就更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程序中应用常识的主要目标陪审团制度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推崇,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行,基于司法审判评估普通民众的常识和价值判断的需要。在调查过程中,陪审团可以做出贡献非职业法人的常识,调整以法官为代表的职业精英的知识和价值观。然而,陪审团制度所面临的陪审团与职业法官之间权力划分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常识与规范权威之间的复杂关系。三、司法审判中运用常识的条件 常识在几乎所有的司法量刑过程中都发挥着作用,但某一内容是否可以称为常识、司法机关如何评价该常识内容、司法机关如何根据常识作出判决,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不同水平的常识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随着每个案件具体情况所设定的具体情景,司法判决的常识含义也有所不同。因此,法官不仅要审查常识本身,还要对常识与待决案件的兼容性做出必要的判断。这些内容是常识适用的条件,也意味着常识的适用是有限制的。 (一)常识内容的规范性必须满足司法裁判的规范性需要。所谓规范性,是指为人们建立行为标准。我们不是解释人们的行为,而是告诉他们他们有权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事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不能直接影响审判的结果。这类常识与法律规范具有协同作用,为司法判决提供了互补的理解。 《合法性》 作者:[美]斯科特·夏皮罗 译者:郑玉双、刘业胜 版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年12月6 例如,当我们说7日晚上发生某事时,这里的“夜”一般指“从黑暗到黎明的时间”。这意味着这一晚包括7日晚上和8日凌晨,在法律上相当于2个日历日。在司法过程中,真正影响判决结果的是常识,包括从社会生活经验中获得的规范指导。例如,人们对合同的常识包括这样的理解:合同必须由至少两个当事人签署,并且合同各方都必须履行。有学者将这类常识称为“规范事实常识”或“制度事实常识”。 《论法律作为常识的制度化》作者:叶一洲版:中国法律出版社2020年6月当我们认定某物为“合同”时,它不仅仅包括对与合同相关的规则和制度的基本了解。还包括人们对应该遵守上述规则的判断。如今,常识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维持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当一方声称某件事是“常识”时,通常意味着人们应该遵守支持它的规则。关于人际关系和行为内容的常识是否符合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尤其是是否不存在隐性偏见和歧视,需要进一步明确。从个体角度来看,人们对常识的获取可以通过系统的知识学习来实现,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经验、自我反思、文化传承中归纳得出结论。它是自发地、自然地形成的。经验意义上的常识是常用的盟友可靠,但并不总是如此。人们的头脑中可能存在伪装成经验常识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以常识之名参与司法程序,本身并不构成常识,即使构成也可以理解为常识,但其规范程度并不能为司法判决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认知贡献。因此,当当事人提出一定程度的常识作为主张的依据时,法官需要做出规范性的判断来回应。例如,在张某与卢某(夫妻)被指控共同诈骗的案件中,卢某的律师辩称,卢某的行为是由其丈夫张某指使的,张某并不知道张某是否有诈骗其粮款的意图,而她按照张某的指示进行的行为符合中国家庭道德和常识经验。这里的经验常识既不是自然法则,也不是原则或原则社会认可的意识。充其量只是当事人的经历和社会的认识。这不符合常识,更不符合司法决策的规范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接受法律体系的价值判断,即使内容被认为是“常识”。比如,在补偿方案中,我国部分地区因房屋征收和移民安置,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受到与男性不同的待遇。虽然这种做法确实可能构成特定群体或地区内部的“经验共识”,但其中存在的歧视性因素与法律秩序相矛盾。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常识引入司法程序。 (二)要使常识的“常态”适应判断的“差异”。学者们发现,法律实践中“常识”裁决的出现有两个前提条件冰。首先,与具体司法或执法实践关系较远;其次,关于具体司法或执法实践的信息不多。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解释这两个条件。在priFirst中,常识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遥远的,这意味着常识本身通常不是案件的重要事实。在欺诈案中,被告声称某些宝石具有神奇的特性和价值。常识表明,被告声称的魔法石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这部分被排除在证据之外。但无论被告是否构成诈骗罪,更重要的是判断被告是否捏造事实、非法占有财物,骗取他人欠款。其次,本案缺乏充分的直接证据,现行法律规定给常识的适用留下了空间。 F又比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结合刑事措施来判断被告人应对死亡后果的主观状态。这是因为他的基本常识被浓缩成犯罪工具。刀具、枪械等立即致死、逐渐致死的毒药等,可能反映了被告人对伤害程度的预期。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被告人使用的鱼叉或砍刀与受害人的多处撕裂伤或穿透伤相符,就可以明确判定主观故意。在这些案件中,鱼叉、砍刀以及受害者的多处割伤和穿透伤都是重要的证据。法官结合常识和这些重要的测试来推断犯罪的主观意图。当直接证据确凿,或者常识的内容与案件的重要事实一致时,常识的作用就不那么突出了。推论结果与社会普遍认知一致。 “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这是生活中的常识,通常很难对案件的侦查做出多大贡献。在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声称因过量饮酒导致死亡是因意外伤害,因此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法院认为,过量饮酒有害健康是生活常识。法院认为,饮酒行为本身不满足意外伤害所包含的外在的、突发的、非自愿的因素,认定其不构成意外伤害。本案常识内容的普遍性已达到与案件事实的特殊性相适应的状态。正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饮酒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酒精的影响也随之而来。赔偿应当在当事人的意识范围内,事故造成的伤害之间的界限应当明确。判断常识与待决案件是否相容,关键在于常识的内容是否有助于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内直接回应具体案件的事实争议。例如,日本《汽车事故责任保险条例》规定了酒后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这样的常识在解决责任纠纷中没有立足之地。在抢劫案中,法院发现,侦查机构根据齐木林辨认的尸体倾倒地点进行了调查实验,辩方也根据齐木林辨认的地点分析了尸体的漂移轨迹。根据扶余市气象厅的分析,该物体废弃于富春江东武大桥南岸,特别是南岸附近。废弃物品可能滞留在桥附近的南岸。这个分析符合常识。法院采纳日本气象厅的意见可以理解,但日本气象厅的分析是专业意见,常识是一般认识。仅通过与常识进行比较,无法确定日本气象厅的分析是否可以被采纳。此外,法院在此并未确认任何常识。换句话说,用常识来解释日本气象厅专家意见的可接受性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众所周知,在道路交通领域,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距离是强制性的,也是驾驶时的常识。这一要求主要是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通常包括这样的先决条件:您的一方不会对他人的驾驶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前述青岛行人碰撞事件中,案发现场视频显示,两名行人均未注意观察,均做出严重影响他人的动作,且未包含驾驶场景。我们看到,法官所表达的常识性陈述与证据和事实不符。审判中可能存在多个事实问题,可以使用常识来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这一事实争议是一个重要事实。即使没有这样的事情,常识和司法判例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可以共存的。有专业人士指出,常识性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且是片断的。与构成犯罪的证据相比,它在案件的证据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非中心位置。仅凭常识证据几乎不可能证明案件事实。电影《Article 20》(2024 年)剧照。在强奸案中,上诉人辩称,性关系是双方自愿的,不构成强奸。法院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监控录像包括:视频数据、检查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确认。法院还认定受害人的性取向为女同性恋,并认定辩方的“武断”意见无法明确表达,有悖常理、常理和传统智慧,因此无法成立。本案中,涉案证据构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完整证据链,并以围绕“受害人是女同性恋”形成的常识性判断作为实质性和全面性的依据。强化证据有效性。综上所述,常识的“恒常性”决定了它只是某些社会关系的共同内容,而每一个案都是特殊的。常识通常与特定案例中必须证明的事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司法机关只有明确常识与需要证明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适用常识。 (三)违背常识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讨论。在司法程序中,当遇到普通的分歧和争议时,换句话说,有理有据的论据通常被认为比无理据的结论更可靠。这至少会要求法官相信这些说法,也会减少他们在未来案件中做出决定的自由。在司法程序之外,辩论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听众的尊重,可以凝聚更广泛的共识,增强司法公正。红色性。司法诉讼争论根本上需要解决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特殊关系。无论是法律的适用还是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都必须提供理由或理由来支持其结论。这已成为共识。刘星教授曾说过,在日常生活中,用“经验和常识”去尝试事情是很困难的。他指出,法律程序可能会很困难。其根源在于,法律辩论比日常生活中的辩论更能揭示利益和是非立场的复杂性。法庭诉讼中讨论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比日常生活中受到更多的审视、期望和要求。司法逻辑:实践中的方法与正义 作者:刘星 版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5 年 11 月 如上所述,常识的明显性质为司法程序中常识的运用提供了初步的合法性。如果司法程序的各方及其潜在的支持者都不质疑常识的内容及其适用,那么此时就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正如常识的内容存在差异一样,常识的显而易见程度也存在差异。运用常识并不能完全免除司法机关的抗辩义务。当常识的应用受到质疑时,需要进行合理的辩论。一些学者指出,“只要基于‘常识’,即非专家的理性推理和常识,对判决的审查就是自由的”。这句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意味着常识是衡量法官举证责任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人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判断常识的储备情况审判中的人和受众也不同。当司法程序中出现常识性分歧时,辩论是必要的。诉状的直接目的是通过诉状回答当事人的常识性问题,达到司法判决的目的,凝聚法律界的共识。尽管常识在司法判决中的运用并不一定是核心;一旦司法判决偏离常识,就会对公众对正义的稳定预期产生强烈影响。因此,法官也必须关注公众的反应。与专门的法律判断相比,常识性问题没有专业障碍,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争论。法官在针对公众的辩论中使用的资源和辩论策略也应该不同于针对专门话题的辩论。最有效的论证策略是用一种常识来解释另一种看似荒谬的事实,即将不寻常的事情归咎于另一种常识。如果法官的判决违背常理,即使法官对他的判决感到满意,l的论证负担也会很低。らに重くなる。在抢劫案中,被告称自己去早市买了红针。法官指出,红枪鱼生长的最佳温度是20至26摄氏度。案发时间3月13日上午8点左右,由于气温不适合马林鱼生长,没有人出售马林鱼。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不过,红马林鱼是观赏鱼,而非食用鱼,一般大众对其适宜的生长温度了解不多。只有经常养鱼的人或者专业养鱼的人才会明白这一点。当法官将这种不太普遍的知识称为“常识”时,需要进一步了解解释是不可避免的。电视连续剧《胜利者是对的》(2012) 的框架。在一场外观设计专利纠纷中,一家公司认为其外观设计专利受到侵犯。外观设计为一款手持花洒产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普通消费者的知识和认知能力,淋浴喷头产品必须包括淋浴喷头和手柄两个主要部分。这两种设计特征在使用过程中易于直接观察到,构成了花洒产品整体视觉效果的基础,赋予了产品设计美感。因此,认定两种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存在显着差异,不构成相似。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按钮虽然可以有多种形状,但其在手柄上的位置主要是基于功能设计,不会明显影响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新审判决h众所周知,吸嘴、手柄及其连接部件是容易被普通消费者看到的部件。按钮的作用是控制水流开关。普通消费者在看到花洒手柄上的按钮时,不仅会考虑该按钮能否起到控制水流开关的功能,自然也会关注其装饰性,考虑按钮的设计是否美观。在本案中,三级法院从普通消费者的经历出发,但结论和推理却有所不同。其中,二审裁决受到当事人质疑,称其“有悖常理”。确定哪些决策“违背常识”需要仔细讨论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此案在三级法院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虽然不能说结论的唯一正确性是在绝对意义上得到了证实,如果我们反思前两次审判的句子,新审判的句子中通过论证过程表达的常识判断显然更可靠。剩下的观察:常识的辅助地位和理性的运用。常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认知系统。常识是社会经验的结晶,内容极为丰富,对司法程序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常识的运用必须继续辅助事实的调查。根据具体情况,常识的作用必须与证据结合起来。 《明清民事审判与民事合同》 编者:王亚新、梁志平、赵静 编者:禾木出版社,2022年5月 当事实分为直接客观事实和背景事实时,在司法审判中,基于常识对事实的调查往往会被忽视。功能作为背景事实。即使常识作为排除事实,一般也不构成案件的重要事实。在另一些情况下,常识作为评价证据和推断事实的基础,其主要作用是促进证据事实转化为最终的判断事实。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识无法完成认定案件事实的任务。在个人层面,基于常识的判断通常以直觉的形式出现。这种综合直觉的机制极其复杂,包括法官在内的直觉主体并不一定能准确把握这种直觉的本质和正确性。因此,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适用,其可靠性都不是基于个人的常识直觉。法律、证据和相应的规则构成实质性常识判断的局限性。从司法论证的角度来看,司法裁判解决纠纷的目的是特殊的、具体的。由于常识的普遍性和普遍性,它主要作为论证中的基本一致,但很难将其用作客观一致。在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常识的作用更加有限,有些案件的事实必须通过专业评估等特殊程序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律和常识无法得出结论时,司法机关只能选择接受技术权威的意见。专业化程度越高,常识的作用就越有限。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已经走得太远了。”经验压力下,司法实践中出现另一种趋势:司法机关过于依赖身份核实等专业判断,抛弃常识性判断意见和“常识判断的功能逐渐弱化”。电影《证人》(2013)剧照。现代技术与常识之间的复杂关系相互促进、相互竞争,但常识的边界在不断转移,专业判断与常识推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如果司法过度依赖技术权威,忽视常识的普遍性,法院的社会认可度就会下降,可能导致“司法贫困”的困境。传统常识司法意见的不断出现,进一步强调了在个案中准确运用常识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常识的运用必须积极、谨慎,保持规范考虑、案例适应和讨论必要性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在涉及的情况下在价值观冲突的情况下,常识应该服务于法律体系的总体目标,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按照之前的顺序。当然,常识对于正义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常识理性始终为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常识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不仅为行为提供了基本准则,而且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朴素智慧、信仰和意识。在常识、法律规范和技术权威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常识允许我们识别和区分基本社会信仰和个人偏好及任意假设,避免司法决策出现不合理的偏差。常识的合理性总是邀请我们进行实际反思。在复杂的社会概念中,“我们分享什么,我们应该分享什么”这是常识对于司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最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常识和理性的基础上,司法机构、法律工作者群体和公众之间才能建立信任和良性互动。法律只有植根于日常生活,才能保护人们日常生活中珍视的价值和意义。【来源】吴非:《论常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第172-183、192页。 作者:吴飞(山东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 此事点评: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