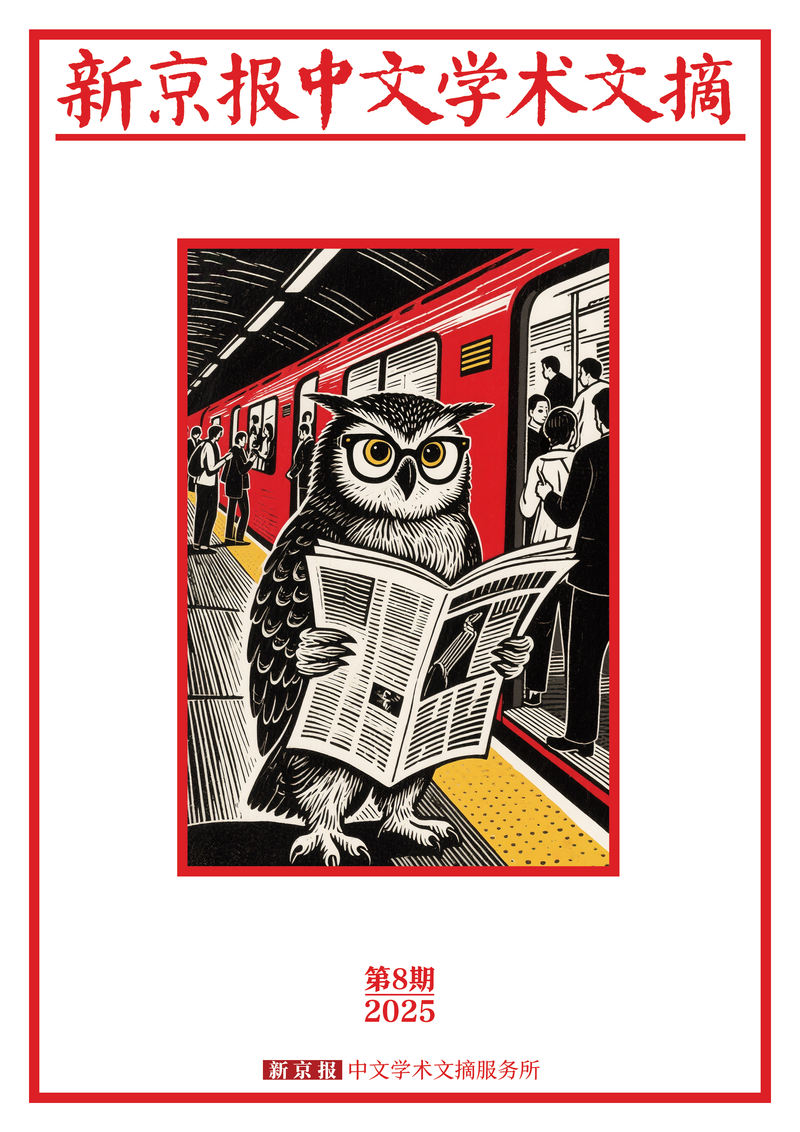 “槟榔的食、药、俗三大文化特色,不是一蹴而就的。” – 王仁政和于134-145。本期评述:摘自陈英芳文:罗东 现代社会,除了书籍之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另一个基本手段。今年8月以来,《京报书评周刊》拓展了以书评为基础的“学术评论与摘要”的知识传播工作,并筹办了“京报中文学术摘要服务”,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杂志业和《人大报纸副刊》、《中国社会科学摘要》等摘要刊物提供服务。每周出版一期,每期推荐两篇文章。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最新、专业、前沿的文章。我们也希望入选的文章具有清晰的本土和全球问题意识,具有独特的中文写作气质。这次是第八期,本期节选的是中国社会史研究文章。作家王仁政、余新忠则追溯历史,从“人地互动”这种相对普遍的生活方式的角度审视槟榔文化。在餐馆、公交车、公园等地方,嚼槟榔的人随手打开一盒槟榔,拿出一个花生壳大小的干果,开始慢慢咀嚼。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槟榔中毒引发癌症的隐患等问题,对于禁止销售槟榔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槟榔虽然有很多弊端,但为何如今如此受欢迎呢?两位作者讲述了槟榔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食品、药品、礼品三种作用。以下内容经广东省社科公司许可转载。摘要、表格、参考文献。有关贡献和注释,请参阅原始出版物。作者:王仁正、余新中电视剧《结婚公告》剧照(1998)。近年来,由于宣传嚼槟榔(Alecacatechu L.)致癌,各地不同程度地掀起了抵制槟榔消费的浪潮,有的甚至以禁止槟榔、下架等武断行为干预市场,试图从市场消费层面消除这种社会不良习惯。另一方面,这些市场干预和消费者抵制也反映出槟榔消费市场的庞大。这也让你思考,为什么这种看起来或味道都不太好的水果,在当今以胃口为重的饮食环境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d.现在嚼槟榔已经不是什么风气了。传统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盛行嚼槟榔的习俗。目前槟榔种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槟榔礼仪和习惯的构建,以及槟榔礼仪和饮食习惯的传播及其文化含义的探讨。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有关槟榔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从人类文化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槟榔的案例。学术界作为槟榔文化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者,仍然忽视了槟榔文化构建过程中“人地互动”的因素。所谓“人地相互作用”,是指人类在改变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它还强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槟榔自作为地方作物传入中国以来,就被赋予了多种社会属性,如日常咀嚼食品、各种药物的药用原料、社会习俗中的水果礼品等。槟榔社会属性的多样性源于其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文化特征不仅是槟榔的独特属性所赋予的,也是“人地互动”下文化建设的结果。因此,本文从“人地互动”的角度审视槟榔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基本含义,试图提供与以往不同的解释。 1.槟榔食性的区域差异特征及环境依赖性。 《中国图书》(12卷)作者:【汉】班古译本:【唐】颜师古璞blisher: Chuka Publishing Company 1962年6月 槟榔主要产于北回归线以南温暖的丘陵山区,以海南省和台湾为主要产区。中国书籍中最早记载的槟榔,见于汉代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六洛兮、人品、鲁”。颜师古先生曰:“冷平即宾焕。”这里的“Lemping”是槟榔的别称。 《三州黄图校正》作者:何庆谷编:中华书社2012年12月据《三州黄图》记载,汉武帝灭南越国后,迁了一百多颗槟榔种植在福利宫内,供观赏之用,但并无农作物价值。后来,由于福利宫气候不利,槟榔大部分从内部枯萎,所以于益期说槟榔“经不起霜冻,不能种植”。北方有槟榔,但必产于海南。”此后,任何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北方第二次种植槟榔的情况。《三府皇族》记载,当时岭南地区已有槟榔。云南南部也有零星种植槟榔的情况。李昉《太平御览》引《云南记》云:“云南有大肚槟榔。”满书也提到:永昌、丽水、长邦、金山等地盛产槟榔,《临摹代大》载:“海南立东产槟榔。”宋代贬官诗文中,槟榔成为海南的地域形象。 《南都辞琼观》描述了宋代海南岛上广泛种植槟榔,槟榔也成为重要的农作物。槟榔是海南岛与内地的重要贸易项目,每年有数百万颗槟榔出口到福建、广东等省份。 《虞集集》(8册) 作者:[宋]王祥之 版本:中国图书公司,1992年10月 从历史上看,槟榔种植的北界基本上不超过长江以北。槟榔作为亚热带植物,需要严格的光热条件才能生长。北回归线以北的气候不适合种植槟榔。槟榔生存环境的限制是由于传统时代槟榔食食习惯的地方特点造成的。我赋予了他存在的特征。在出产槟榔的热南地区,槟榔是老百姓的“常见食品”。郑刚曾写过一首诗,名叫《语言》。 “拌、嚼、饕餮”是指海南人乱吃槟榔的习惯。何范成达去广州旅游时,他还把满街都是血槟榔的污迹误认为是血迹。产区的优势支撑了当地槟榔的生产和消费。在广东南海,人们“经常吃槟榔,一天吃几十天”。不过,吃槟榔的习俗并不只限于雷南。 《岭外大达》中记载:“川、粤、闽西路,食槟榔”。 《与事记》还提到,泉州人有以吃甜菜代替茶的习惯。六朝时期,江南贵族中曾短暂盛行过口吃槟榔的习惯,可见当时江南士人中已有吃槟榔的习惯,如刘米之求槟榔、任凡父子为“槟榔爱好者”、萧逸命子以槟榔供灵祭祀等。办公室。因此,郭说认为,江南吃槟榔在南朝时期就从“洋俗”转变为“吴俗”。然而,当我查阅各种史料时,都没有提到江南种植槟榔。据民间吃槟榔的记载,南朝时期江南吃槟榔的人多为贵族。电影《青槟榔之味》(2006)的剧照。为什么六朝时期吃江南槟榔的习俗没有在民间流传呢?中国内陆流行的槟榔主要是海南槟榔。答曰:“(槟榔)为海商所售,琼官所收,每年数量达十次之多。”宋代,航运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泉州与海南之间往来的泉州商船大部分在正月期间从泉州出发前往海南并返回香港五月和六月。若惠森商船载有新鲜槟榔,将于4月返港运输。当时,槟榔贸易成为琼州城的重要收入来源,以至于有“国无槟榔之利,不成国”之说。虽然它不是大宗货物,运输难度较大,但跨海运输所产生的劳动力、物资、税收等成本,对于槟榔贸易来说都是额外成本。此外,槟榔还从福建运往广东。江南两地之间运输槟榔需要长途陆运,费用昂贵。槟榔只在江南文人中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六朝时代奢侈盛行的社会环境。六朝时期,槟榔不被崇拜由于在北方种植,运往北方的成本太高,所以长期被北方统治者使用。沉约在胶州受赠槟榔一千颗。六朝文人的言辞中,常常表达对槟榔的感激之情,如王胜儒的《谢谢你赐予我的槟榔》、于建武的《谢来槟榔气》、《谢东古来贝果气》等。 《全粮文》作者(主编):【清】严克俊编:商业出版局1999年10月,槟榔因其特产和赏赐的双重地位,成为崇尚奢华的六朝文人中的奢侈品。江南文人中谈论槟榔的习俗,也松散地形成了一种消费分类。也可以说,这种消费分类是学者与普通人的一种区分方式。普通人,就像普通人一样槟榔自然被排除在食用槟榔之外。除了成本之外,六朝时期江南吃槟榔的习俗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常见食物。到了宋代,吃槟榔的习俗在江南贵族中逐渐消失。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江南地区几乎没有人们吃槟榔的记载,所以郭说说槟榔成为“吴风”,应该说是“吴学者的习惯”更为贴切。最相关的记载与台湾吃槟榔的习俗有关。它出现于明末,与当时台湾张、全、赵等人的移民活动有关。清朝时期,吃槟榔的习俗流传到湖南、北京等地。湖南人吃槟榔的习惯在湘潭比较盛行。强光年间,槟榔开始成为日常消费食品。为湘潭人民服务。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作为湘粤贸易通道的地区在羌朝时期蓬勃发展。在北方,北京槟榔的饮食习惯最为盛行。清朝中期,豆沙包在北京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清朝皇室也喜爱槟榔,嘉庆皇帝也有吃槟榔的习俗。但由于槟榔原产地的奇特性、距槟榔原产地的距离等因素,清代中期北京的槟榔习俗只流行于上流社会。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逐步形成,它才开始衰落。 《北京民间传说百图》中有一幅卖槟榔的图,图上的解释是:“安南、海南的浆果,藏在柜子、笼子里,在街上卖,吃着。”这表明槟榔在清朝末期就出现在北京市场消费中,大部分是从海南、越南等槟榔产区进口的。《北京民俗百图》(北京图书馆出版处,2023年版)清代槟榔售卖图解。槟榔的食用习惯虽然在清朝南北地区有零星分布,但在清代之前随着近代食品工业技术的介入,槟榔食用习惯的地域分布普遍趋于缩小。清朝末年,吃槟榔的习俗逐渐消失,清朝灭亡后,北京吃槟榔的习俗也逐渐消失。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除海南、台湾等部分地区外,传统的口服槟榔已被工业加工的风味槟榔所取代。风味槟榔因其便于运输和储存而畅销全国各地。产槟榔的海南岛和台湾,生活在炎热潮湿的热带环境,仍然有人愿意咀嚼新鲜槟榔来消化食物、消暑。由于槟榔具有成瘾性,咀嚼新鲜槟榔的习惯在这两个地方得以延续。因此,用篮子叶和酸橙吃新鲜槟榔的传统在海南和台湾仍然流行。地理环境限制了长江以南地区槟榔的种植,排斥了槟榔消费群体。福建、广东产的槟榔南下后,只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流行。六朝时期。相反,在福建、广东等槟榔盛产地区,槟榔却是日常咀嚼的“常见饵料”。在湘潭,清朝时期商路发达,商业活动繁盛,吃槟榔的习俗逐渐流传开来。虽然当时不产槟榔,但由于地理优势,吃槟榔的习惯迅速传播开来。由于交通条件较好,贸易逐渐繁荣,南北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清末北槟榔习俗逐渐在民间流传。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所画的清代中国槟榔摊。近代,随着食品工业技术的介入,工业化生产的槟榔因其便于运输、易于储存、风味浓郁、提神醒脑的特点,成为许多辛勤劳动者的爱好。精神。此举风靡全国,打破了环境因素对槟榔饮食习惯的限制。环境差异影响不同地区和季节的槟榔消费模式。这种差异也反映了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的地区环境导致槟榔消费群体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影响各地区槟榔消费规模。同时,我还表明槟榔的消费高度依赖于环境。消费规模和可持续性受生存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2.影响槟榔药用知识形成和“吃槟榔祛瘴”认知的环境因素。 “外事纪事”页面内。杨复《外事实录》云:“若割表皮,煮皮,热之。渗入其中,就会变得像干枣一样坚硬。用古槟榔的灰,吃了它,就会减少能量、食物、白虫,消除槟榔。饮当当饮。”这说明当时的岭南人认识到吃槟榔有理气消食、驱虫的功效。岭南、江南人民咀嚼槟榔,可能与此功效有关。中草药有“药食同源”的传统。槟榔不仅是“食”,还被尊为南方四大药材之首。作为医药,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东汉张仲景的《清桂药诸药方》中就有“四时解五脏热,调芙蓉汤用量方”,其中以槟榔四颗入药。《本草经》(第二编) 作者:[唐]苏静 其他版本:安徽省科技出版局 2005年9月,槟榔开始入药。三国时期,李当之在《药书》中写到槟榔,称其为“槟榔之门”。隋唐时期,槟榔被列入“新材料药物”,列为木材部门的中间产品,并获得批准宋代时,槟榔入药方兴盛,《太平额民洼吉术方》中就有30处槟榔入药,在同时期的其他医书中,如《小儿新书》、《钱之诀》、《苏陈良方》、《薄济方》、《证类本草》等也经常使用槟榔入药。 《点心应用方》、《济生》将药物分为“泻气”、“祛风”、“补虚安”四类。其中,方剂以“泻气”为主,共15方,包括“安息丸”、“丁辰元”、“和胃丸”等,其余15方主要以解积热、消小腹、祛风除虫、补虚损为主。其实,汉末医家已经总结了《名医比尔》云:“槟榔味辛温,无毒。主要用于去谷、逐水、去水、去尸、治白斑等。”后世使用槟榔的方剂,大多都逃不过这样的药性概括。唐宋时期,槟榔还经常用于针灸治疗创伤的方剂中。《盖代秘笈》中记载了以槟榔入药治疗金疮的方剂。另外,《外科文摘》中收录有《生消散》、《生肌散》、《胃极保鲜》中收录有《生楼膏》、《麝香膏》、《白五膏》等处方,均使用槟榔。就像医学一样。 《黄帝内经素问》云:“痛痒疮毒,必治”。 “它属于心。”心主血脉,属火。也有人说,如果阴气不遵循人体的规律,就会出现癫痫和肿胀。王兵曰:“阴气逆,血瘀也。” “因抑郁而积热流脓的病症称为炭疽。”认为疼痛、肿胀主要是营气逆、血气郁滞所致。传统医学认为,槟榔具有理气补虚的功效,值得推广。为什么要用槟榔做药材治疗伤口的药物。唐朝中后期,槟榔还被用来治疗瘴气。在外台秘药中,有“木香犀角肝”的记载,以槟榔入药,建议定期服用。它可以“预防各种致命的瘴气和毒物”。此后,在《苏陈良方》、《传心适用方》、《太平惠民和基础方》、《生机总录汇编》、《瘴疟指南》等医书中频繁使用。见郑全旺认为,槟榔入药治疗瘴气,是因为它具有“行气、祛积、化痰”、“下气”的功效。此证的原理是“气衰”。作者:【唐代】王涛注:高文柱主编:学苑出版社2011年1月 宋代《任治志》《治脚气》中也经常提到槟榔可以治疗脚气。孔塔书中收录了50余种治疗脚气、脚痛的偏方,其中13种以槟榔入药。 “脚气”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张仲景《金匮要论》中记载的“附子”和“鹿米司”两汤中。克弘认为,“脚气”首先产生于岭南,后传入江南。 “风吹来的温暖、潮湿、有毒的空气首先传到脚上,然后从下往上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叫脚气的原因。”唐代孙思邈也认为,脚气的病因主要是“风毒”。又提出,干脚气“风毒在经”,湿脚气“湿脚气毒在经”,仍将脚气与风毒联系起来。据《川崎办处方》,松色王朝表示,用槟榔治疗运动员的风湿病是合理的。那时。因此,李时珍认为槟榔有“祛诸风、降诸气”的功效。点击本版)” 作者:【明代】李时珍 版本:人民医药出版社,1982年11月。吃槟榔可以防瘴气的认识,最早见于郑纲中的《梆》诗。这里的“毒雾浓雾”就是指瘴气。稍后,周去非在《灵外带大》中记载,交子吃槟榔可以防瘴气。瘴气:“(吃槟榔可以防瘴气)。槟榔)防瘴气,下气,消食。如果吃的时间比较长,一定要马上吃。这是吃槟榔时出现戒断反应的最古老记录。另有资料显示,宋代时,礁溪人口服槟榔防治瘴气。罗氏《大教和林录录》中也记载:“岭南人以槟榔代茶,相传有预防瘟疫之效”。这是罗关在岭南的所见所闻,进一步证明槟榔能防治瘴气的知识在岭南早已为人所知。在古代医学文献中,“瘴气”一词最早出现在《神农》中,并出现在《本草纲目》中,瘴气与岭南的关系始于隋唐时期。各种医学文献。他们都宣扬瘴气。理论化,赵元方认为瘴气“生于岭南”,皆为“岭南山岳”,“西源灵章之湿气毒气”。瘴气铭刻于当地风俗之中,隋唐时期,罢官贬官的知识传播开来,岭南瘴气地区的形象也日益加深。电影《奶奶的伯特利》(2017)的静态图像。在雷南人为构建的瘴气区地域意象下,刻板的地域意象促成了瘴气区与瘴气区之间的关联。n 槟榔和瘴气。这种联想出现后,吃槟榔祛瘴的认知也是在槟榔作为祛瘴药的作用和岭南瘴区形象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六朝江学者对槟榔食南的认识,仅着眼于泻气消食。比如,当刘米芝向妻子江哥要槟榔时,江哥开玩笑说:“槟榔可以帮我吃饭,但我总是饿,为什么要这个呢?”这种认识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前面提到的《南方植物》等地理书籍中记载的槟榔的好处。槟榔饮食习惯的传播高度依赖于贸易路线,因此这种饮食习惯很容易因贸易路线的中断而受到干扰。这可能与唐宋以后吃槟榔的习俗在江南消失有关。自从客户唐宋时期江南废除了吃槟榔的习俗,江南士人只能了解角槟榔的消化作用。后来的“吃槟榔防瘴气”的认识,并没有出现在六朝时期江南吃槟榔的士人群体中。早在汉晋时期,医家就开始用槟榔入药,认为槟榔具有理气消食的功效。唐宋以来,槟榔常用作理气、祛风、防瘴的药物。这为后来岭南人认识吃槟榔预防瘴气奠定了基础。最新研究还表明,槟榔中至少含有六种生物碱,包括槟榔碱、槟榔碱、去甲基槟榔碱、去甲基槟榔碱、异去甲基槟榔碱和高槟榔碱。槟榔碱刺激神经系统,给人一种感觉健康,增加唾液分泌,促进胃肠蠕动,促进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医学文献中对槟榔降气消食作用的总结相对应。槟榔原本是一种口服食品,具有“卫生”的含义,因为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反馈与入药的疾病特征是一样的。咀嚼槟榔可以增加咀嚼者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停止咀嚼会导致咀嚼者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其精神状态。因此,长期咀嚼槟榔会产生耐受、渴求、戒断等症状,助长身体对槟榔的依赖。由于“卫生”和咀嚼癖的共同作用,吃槟榔已成为岭南地区普遍的饮食习惯。孩子饮食习惯的出现也是形成的关键与槟榔有关的习惯。此外,槟榔入药的区域趋势也很明显。槟榔最初入药时,只有理气、消食、杀虫的功效。唐宋以后,医家开始越来越重视地方病,并遵循“泻气”、“祛风”的对症思想,用槟榔入药治疗瘴气、脚气等岭南地方病逐渐成为医家的普遍共识。因此,自唐宋以来,槟榔就被普遍用来治疗瘴气、脚气。槟榔自作为理气、祛风、防瘴之药,到槟榔防瘴知识的形成,是人类长期适应生存环境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种文化和生理上的选择ngnan 人根据他们的环境做出反应。这也是隋唐时期岭南瘴气地区的区域形象定型后形成的认知。这种意识是人体对自然环境的感知结果。结果也是环境塑造人类文化行为的过程。它们都体现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中人类行为“形成”的过程。 3、槟榔仪式和人类建造过程的粗俗表达。 《通源》作者:【唐代】杜佑注释,编辑:王文进等版本:中华书局,2016年4月 吃槟榔的习惯是槟榔礼俗形成的基础。传播槟榔药用知识和食用槟榔防瘴知识,是传播槟榔礼俗的关键。最早的槟榔礼俗记载现存文献中的oms可以在《南方植物》第二卷《异物》中引用的文章中找到。 “(槟榔)从临邑出来,别人都认为它是高贵的,婚礼的客人必须先走。如果不安排见面,就用相互仇恨的话。”这里,“槟榔嫁”是临沂的习俗。后来在《通典》中,杜宇还提到,“葛鲁鲁王国”的婚礼习俗是“第一次求婚时只能用槟榔作为礼物”,而这种登记也是域外的习俗。到了宋末,槟榔已逐渐成为“中华风俗”。例如,陈敬一在《泉芳北图》中描述了中国南方的一种习俗:“男子聘用女子,必以槟榔为礼,宾客相聚,必先带槟榔,若不用槟榔,则互相憎恨。”宋代吴谦被流放到浑州时曾写道:“巫师用他们的”这也解释了中国赠送槟榔的习俗。咸州民间传说。从一般情况来看,“聘槟榔”应该是最主要的槟榔礼仪形式,明清时期在两广地区最为普遍。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泗州,“嫁娶不用媒人,而用槟榔”,广东南雄县“嫁娶用槟榔”,惠州县“旧婚订婚用槟榔”,潮州县“鸽果为喜食,作结婚贺礼”。所有槟榔在婚礼仪式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富川、平乐、恭城、武宣、北流、雷州、电白、灵山、增城、阳江、广宁、化州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在广东省的凤川、华化、新会、象山、德清、茂名、吴川、清远、信宜、阳山、恩平等地也有承包槟榔的习俗。 《采槟榔图》(清代,不详画家)的一部分,描绘了云南省少数民族采摘槟榔的情景。近代以来,广东、广西两省食用槟榔的人数明显减少。与此同时,用槟榔招人的习俗在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逐渐消失。但海南仍然有这样的遗产。在海南省一些市州,点名聘人仍被称为“讨槟榔”或“摘槟榔”,并仍以槟榔作为礼品。作为礼物,槟榔也经常出现在葬礼上。例如,在云南天岳,人们用槟榔和甘蔗籽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我在广西北流,人们用槟榔香和蜡烛表达哀悼。在广东省澄海市,“慰问”用槟榔和蜡烛来表达感情。 “槟榔,槟榔。”福建省泉州,“las nueces de betel se utilizan como obsequio a los amigos del pueblo para celebrar la buena o la mala suerte”。在海南岛的一些市县,槟榔在丧葬活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婚礼的服装和葬礼、宴会的邀请和团体的各种活动中的“公社”原则都是重要的。分享槟榔的可能性为习惯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这是槟榔的“自定义”属性。清王朝的惨痛教训,湖南湘潭的槟榔人物编号和其他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随后,“槟榔”逐渐融入湘潭人的礼俗之中。例如,湘潭过年时会赠送槟榔作为拜年礼物。槟榔也可作为结婚礼物水果。在许多礼仪场合,槟榔被用作馈赠宾客的礼物。这与广东、福建、海南等省的槟榔习俗十分相似。 《福建通志》(编)作者:【明代】黄忠昭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槟榔的饮食习惯不能与槟榔的礼仪习俗划等号。槟榔礼俗强调槟榔作为馈赠水果的文化作用。在礼俗中,槟榔参与仪式。作为一种饮食习惯,槟榔无非是一种口头传统。 coStumbres 是依赖于社区成员必须遵循的传统力量的标准化行为。形成槟榔礼仪也受到传统力量的影响。关于文化 作者:[英文]马林诺夫斯基 译者:费孝通 版本:华夏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1月 当一个社区有共同的饮食习惯时,这些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该社区大多数成员行为的驱动力。槟榔礼仪的形成就是在这些社区习俗的推动下形成的。由于槟榔产于岭南及西南部分地区,因此槟榔被用作辟瘴、防疫的手段。在某些虫害肆虐的环境下,“送槟榔”逐渐成为一种社交礼仪,让槟榔变得“可分享”。这种“共享性”是建立在与环境互动的基础上的。槟榔的共享使其成为人们日常交往中的“社会共享物”。热南槟榔习惯的形成背后有着明显的内在驱动力。换句话说,人们吃槟榔是出于“卫生”的原因s,出于抵抗瘟疫的需要。这是宋代相信槟榔能祛瘴的信念所驱动的“个人自觉行为”。而当这种“个人自觉行动”演变为“集体自觉行动”,即社会“大多数”认识到槟榔可以防治瘴气时,槟榔礼俗就诞生了。这个逻辑也可以解释湖南湘潭等地区槟榔习惯的形成。湘潭槟榔:战争疫病说、药材市场说、风水说、槟榔仙人说。其中,战争瘟疫说、药市说、槟榔仙说等都与瘟疫流行有关。这表明湘潭人吃槟榔,很可能能抵抗瘟疫。因此,凭借靠近岭南、有商路支撑的优势,吃槟榔在湘潭人中越来越普遍。随着普通人的成长在消费群体中,槟榔逐渐成为湘潭人的“社交交换对象”。吃槟榔、“送槟榔”逐渐成为各种社会场合的“自觉集体行为”,并作为送礼融入当地礼仪活动,从而形成了当地槟榔标签。其世代逻辑与热南地区槟榔礼俗的世代并无不同。 198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流行歌曲《摘槟榔》(张野演唱)做背景。由于槟榔不是土特产,所以江南地区槟榔的消费者仅限于社会上的少数贵族。吃槟榔的习俗尚未形成相应的群体基础。六朝时期,江南士人认识到吃槟榔仅限于消气消化食物的目的。而且,在江南,吃槟榔的习俗已经消失了自宋代以来,槟榔习俗的推动力微乎其微。这就是原因。在江南地区,有吃槟榔的习俗,但没有吃槟榔的习俗。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由于地域限制,本地不产槟榔,只在北京的部分人群中流行。清末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北京人吃槟榔的习惯逐渐衰落,并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辛亥革命后,北京吃槟榔的习俗就被废弃了。吃槟榔的习俗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之后才形成“自觉的集体行动”并进入仪式。与吃槟榔的习惯相比,吃槟榔的习惯分布更为广泛。在史前时期,吃槟榔的习俗在北方和北方都盛行。南方。如今,吃槟榔的习惯在全国各地都可见一斑,但吃槟榔的习惯仅分布在海南省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区。槟榔习惯的形成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文化反应。然而,很多人并不需要吃槟榔来养成吃槟榔的习惯。借助食品工业化,槟榔失去了传统形象,以其浓郁的风味和引人注目的包装成为可以与香烟区别的国民“零食”。全国各地都吃槟榔。 1930 年代,越南,摘自阮彭将军的《卖槟榔的人》。国内外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人口是槟榔消费的主要来源。中国有句俗话:“槟榔与烟草相结合,百味无穷”。国内生产槟榔已经不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槟榔的消费在其他方面已经超越了传统时代地理环境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人又会吃槟榔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是目前的槟榔消费行为只把槟榔当成一种振奋精神、缓解疲劳、对生理有刺激作用的消遣。得益于现代食品工业,槟榔也被用作口服零食。口服槟榔的目的不再是预防瘴气的卫生手段。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槟榔对人体健康有害。它甚至被认为具有致癌性。此外,现代槟榔消费者性别失衡也是槟榔难以渗透社会习俗的重要原因。根据研究,在t湖南省长沙市和湘潭市是槟榔消费较多的地区,两市城镇居民中,有76.7%的男性和56.2%的女性咀嚼槟榔。在调查的男性样本中,有31.4%经常咀嚼槟榔,而女性样本中这一比例仅为6.7%,远低于男性样本。 2018年,台湾18岁以上男性嚼槟榔的比例为6.2%,女性仅为0.2%,远低于男性。 40岁至49岁人群中,嚼槟榔的比例最高,为5.4%,其中男性占10.7%,女性占0.2%。差距就更加明显了。电视剧《结婚公告》(1998)剧照。据笔者观察,日常生活中嚼槟榔的人以男性居多。此外,由于现代人追求洁白牙齿的审美观,大多数女性拒绝咀嚼槟榔,甚至厌恶男性咀嚼槟榔。有ar其他地区没有相关统计,但情况应该类似。槟榔消费者性别失衡 这意味着吃槟榔并不是这个社区常见的饮食习惯。因此,大多数社区成员的行为没有规范的动力,槟榔很难融入现代礼仪和习俗。换句话说,吃槟榔的习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吃槟榔的习惯却在减少。毫无疑问,传统时期槟榔习俗的兴衰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以雷南为例。清代以前,岭南是一片瘴气之地。槟榔因其具有祛除瘴气的功效,很快成为岭南地区流行的食品。消除瘴气的关键在于改造产生瘴气的地理环境。元明以来,岭南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岭南经济的深化发展和南迁北迁人口的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明清时期的气候干冷趋势,也引起了岭南气候湿热的变化,产生了瘴气。清朝以后,岭南瘴气地区大部分消失。随着现代西药的传入,槟榔、槟榔等传统防瘴药材,逐渐被奎宁、枸橼酸哌嗪、青霉素等高效廉价的抗寄生虫、抑菌药物所取代。岭南人不再需要吃槟榔来防瘴气,吃槟榔的人数急剧减少。结果,嚼槟榔脱离了群体结构,在整个社会层面不再普遍。槟榔习惯也失去了“集体意识”土壤。此外,由于“重大变化“在现代的传统习俗中,原本繁琐的婚丧嫁娶等习俗已逐渐简化,槟榔很难融入到更具社会属性的婚丧习俗中。当地传统吃槟榔婚礼的六礼已被简化得一应俱全,让槟榔婚礼成为过去式。传统时代赋予槟榔的各种意义正在逐渐消失,其背后的“人地互动”元素也在逐渐淡化。因此,槟榔风俗在热南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这也是热南自近代以来槟榔和槟榔习俗衰落的原因。 四、结语槟榔文化属性的生成和演变本质上是历史时空中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文化诠释过程。l 槟榔作为食品、药物和习俗的属性并不是一朝一夕显现出来的。它们是在人类活动和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从“自然”到“文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也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适应生存和文化建构的过程。槟榔食品属性的形成,标志着槟榔作为一种类似兴奋剂、具有减气、消食作用的热带水果正式纳入人与环境相互作用领域。它是人类在适应生存环境过程中做出的经验选择。但槟榔最初在岭南人中很流行,因为槟榔可以在湿热的环境中补充能量,所以他们开始每天咀嚼槟榔。后来,随着南北之间的货物和知识交流更加频繁,有关国家的记录也被传播开来。岭南的槟榔与中医知识。随着知识的传播,吃槟榔的习俗也随之传播。但由于槟榔生长环境的限制,槟榔的习惯只在六朝时期的江南士大夫和清代的贵族中短暂流行过。近代,随着食品工业化的发展,槟榔的习性已经成功超越了环境因素的限制。槟榔入药是槟榔的文化重要性。将经验实践转化为制度化知识。随着各种方剂书籍和本草的传播,槟榔的药用知识已经系统化。但对于脚气、瘴气等局部疾病,仍很难打破用方剂或草药治疗局部疾病的观念,成为灵丹妙药。通过对槟榔的系统认识,人类应对生活环境带来的生理挑战。槟榔入药后,其物质价值也随之增加,赋予其仪式化以认知前提和合理性。与槟榔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相比,槟榔的仪式化更能凸显槟榔栽培建设过程中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伯特利仪式训练不能通过简单的人际模仿或仪式模仿来获得。自然环境决定了槟榔的供应量和食用槟榔的人。热南槟榔的普及,促进了槟榔饮食习惯在当地社区的广泛出现和共同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槟榔习惯。槟榔标签不是文化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同质化的结果基于适应环境需要的集体消费行为的化。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设行动。吃槟榔的风俗曾在江南、江北的一些地区短暂出现过,但由于槟榔食用没有同质化,上述地区并没有形成槟榔仪式和习俗,更不用说模仿岭南等地的槟榔仪式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塑造,不仅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应激”反应上,更在更深层次上对人类社会文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人地互动”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环境决定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些就是基于上述的独立努力以及这些独立的努力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影响。通过“人地互动”的视角来解构槟榔的文化属性,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塑造作用,也可以看到人类与环境在人类文化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人地互动”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基于单一观念推断文化行为模式的现有逻辑,也让我们发现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微妙方面。 【来源】于王仁政 作者:王仁政(南开大学历史学部中国史博士生)
“槟榔的食、药、俗三大文化特色,不是一蹴而就的。” – 王仁政和于134-145。本期评述:摘自陈英芳文:罗东 现代社会,除了书籍之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另一个基本手段。今年8月以来,《京报书评周刊》拓展了以书评为基础的“学术评论与摘要”的知识传播工作,并筹办了“京报中文学术摘要服务”,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杂志业和《人大报纸副刊》、《中国社会科学摘要》等摘要刊物提供服务。每周出版一期,每期推荐两篇文章。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最新、专业、前沿的文章。我们也希望入选的文章具有清晰的本土和全球问题意识,具有独特的中文写作气质。这次是第八期,本期节选的是中国社会史研究文章。作家王仁政、余新忠则追溯历史,从“人地互动”这种相对普遍的生活方式的角度审视槟榔文化。在餐馆、公交车、公园等地方,嚼槟榔的人随手打开一盒槟榔,拿出一个花生壳大小的干果,开始慢慢咀嚼。多年来,人们一直关注槟榔中毒引发癌症的隐患等问题,对于禁止销售槟榔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槟榔虽然有很多弊端,但为何如今如此受欢迎呢?两位作者讲述了槟榔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食品、药品、礼品三种作用。以下内容经广东省社科公司许可转载。摘要、表格、参考文献。有关贡献和注释,请参阅原始出版物。作者:王仁正、余新中电视剧《结婚公告》剧照(1998)。近年来,由于宣传嚼槟榔(Alecacatechu L.)致癌,各地不同程度地掀起了抵制槟榔消费的浪潮,有的甚至以禁止槟榔、下架等武断行为干预市场,试图从市场消费层面消除这种社会不良习惯。另一方面,这些市场干预和消费者抵制也反映出槟榔消费市场的庞大。这也让你思考,为什么这种看起来或味道都不太好的水果,在当今以胃口为重的饮食环境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d.现在嚼槟榔已经不是什么风气了。传统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盛行嚼槟榔的习俗。目前槟榔种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槟榔礼仪和习惯的构建,以及槟榔礼仪和饮食习惯的传播及其文化含义的探讨。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有关槟榔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从人类文化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槟榔的案例。学术界作为槟榔文化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者,仍然忽视了槟榔文化构建过程中“人地互动”的因素。所谓“人地相互作用”,是指人类在改变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它还强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槟榔自作为地方作物传入中国以来,就被赋予了多种社会属性,如日常咀嚼食品、各种药物的药用原料、社会习俗中的水果礼品等。槟榔社会属性的多样性源于其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文化特征不仅是槟榔的独特属性所赋予的,也是“人地互动”下文化建设的结果。因此,本文从“人地互动”的角度审视槟榔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基本含义,试图提供与以往不同的解释。 1.槟榔食性的区域差异特征及环境依赖性。 《中国图书》(12卷)作者:【汉】班古译本:【唐】颜师古璞blisher: Chuka Publishing Company 1962年6月 槟榔主要产于北回归线以南温暖的丘陵山区,以海南省和台湾为主要产区。中国书籍中最早记载的槟榔,见于汉代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六洛兮、人品、鲁”。颜师古先生曰:“冷平即宾焕。”这里的“Lemping”是槟榔的别称。 《三州黄图校正》作者:何庆谷编:中华书社2012年12月据《三州黄图》记载,汉武帝灭南越国后,迁了一百多颗槟榔种植在福利宫内,供观赏之用,但并无农作物价值。后来,由于福利宫气候不利,槟榔大部分从内部枯萎,所以于益期说槟榔“经不起霜冻,不能种植”。北方有槟榔,但必产于海南。”此后,任何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北方第二次种植槟榔的情况。《三府皇族》记载,当时岭南地区已有槟榔。云南南部也有零星种植槟榔的情况。李昉《太平御览》引《云南记》云:“云南有大肚槟榔。”满书也提到:永昌、丽水、长邦、金山等地盛产槟榔,《临摹代大》载:“海南立东产槟榔。”宋代贬官诗文中,槟榔成为海南的地域形象。 《南都辞琼观》描述了宋代海南岛上广泛种植槟榔,槟榔也成为重要的农作物。槟榔是海南岛与内地的重要贸易项目,每年有数百万颗槟榔出口到福建、广东等省份。 《虞集集》(8册) 作者:[宋]王祥之 版本:中国图书公司,1992年10月 从历史上看,槟榔种植的北界基本上不超过长江以北。槟榔作为亚热带植物,需要严格的光热条件才能生长。北回归线以北的气候不适合种植槟榔。槟榔生存环境的限制是由于传统时代槟榔食食习惯的地方特点造成的。我赋予了他存在的特征。在出产槟榔的热南地区,槟榔是老百姓的“常见食品”。郑刚曾写过一首诗,名叫《语言》。 “拌、嚼、饕餮”是指海南人乱吃槟榔的习惯。何范成达去广州旅游时,他还把满街都是血槟榔的污迹误认为是血迹。产区的优势支撑了当地槟榔的生产和消费。在广东南海,人们“经常吃槟榔,一天吃几十天”。不过,吃槟榔的习俗并不只限于雷南。 《岭外大达》中记载:“川、粤、闽西路,食槟榔”。 《与事记》还提到,泉州人有以吃甜菜代替茶的习惯。六朝时期,江南贵族中曾短暂盛行过口吃槟榔的习惯,可见当时江南士人中已有吃槟榔的习惯,如刘米之求槟榔、任凡父子为“槟榔爱好者”、萧逸命子以槟榔供灵祭祀等。办公室。因此,郭说认为,江南吃槟榔在南朝时期就从“洋俗”转变为“吴俗”。然而,当我查阅各种史料时,都没有提到江南种植槟榔。据民间吃槟榔的记载,南朝时期江南吃槟榔的人多为贵族。电影《青槟榔之味》(2006)的剧照。为什么六朝时期吃江南槟榔的习俗没有在民间流传呢?中国内陆流行的槟榔主要是海南槟榔。答曰:“(槟榔)为海商所售,琼官所收,每年数量达十次之多。”宋代,航运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泉州与海南之间往来的泉州商船大部分在正月期间从泉州出发前往海南并返回香港五月和六月。若惠森商船载有新鲜槟榔,将于4月返港运输。当时,槟榔贸易成为琼州城的重要收入来源,以至于有“国无槟榔之利,不成国”之说。虽然它不是大宗货物,运输难度较大,但跨海运输所产生的劳动力、物资、税收等成本,对于槟榔贸易来说都是额外成本。此外,槟榔还从福建运往广东。江南两地之间运输槟榔需要长途陆运,费用昂贵。槟榔只在江南文人中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六朝时代奢侈盛行的社会环境。六朝时期,槟榔不被崇拜由于在北方种植,运往北方的成本太高,所以长期被北方统治者使用。沉约在胶州受赠槟榔一千颗。六朝文人的言辞中,常常表达对槟榔的感激之情,如王胜儒的《谢谢你赐予我的槟榔》、于建武的《谢来槟榔气》、《谢东古来贝果气》等。 《全粮文》作者(主编):【清】严克俊编:商业出版局1999年10月,槟榔因其特产和赏赐的双重地位,成为崇尚奢华的六朝文人中的奢侈品。江南文人中谈论槟榔的习俗,也松散地形成了一种消费分类。也可以说,这种消费分类是学者与普通人的一种区分方式。普通人,就像普通人一样槟榔自然被排除在食用槟榔之外。除了成本之外,六朝时期江南吃槟榔的习俗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常见食物。到了宋代,吃槟榔的习俗在江南贵族中逐渐消失。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江南地区几乎没有人们吃槟榔的记载,所以郭说说槟榔成为“吴风”,应该说是“吴学者的习惯”更为贴切。最相关的记载与台湾吃槟榔的习俗有关。它出现于明末,与当时台湾张、全、赵等人的移民活动有关。清朝时期,吃槟榔的习俗流传到湖南、北京等地。湖南人吃槟榔的习惯在湘潭比较盛行。强光年间,槟榔开始成为日常消费食品。为湘潭人民服务。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作为湘粤贸易通道的地区在羌朝时期蓬勃发展。在北方,北京槟榔的饮食习惯最为盛行。清朝中期,豆沙包在北京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清朝皇室也喜爱槟榔,嘉庆皇帝也有吃槟榔的习俗。但由于槟榔原产地的奇特性、距槟榔原产地的距离等因素,清代中期北京的槟榔习俗只流行于上流社会。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逐步形成,它才开始衰落。 《北京民间传说百图》中有一幅卖槟榔的图,图上的解释是:“安南、海南的浆果,藏在柜子、笼子里,在街上卖,吃着。”这表明槟榔在清朝末期就出现在北京市场消费中,大部分是从海南、越南等槟榔产区进口的。《北京民俗百图》(北京图书馆出版处,2023年版)清代槟榔售卖图解。槟榔的食用习惯虽然在清朝南北地区有零星分布,但在清代之前随着近代食品工业技术的介入,槟榔食用习惯的地域分布普遍趋于缩小。清朝末年,吃槟榔的习俗逐渐消失,清朝灭亡后,北京吃槟榔的习俗也逐渐消失。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除海南、台湾等部分地区外,传统的口服槟榔已被工业加工的风味槟榔所取代。风味槟榔因其便于运输和储存而畅销全国各地。产槟榔的海南岛和台湾,生活在炎热潮湿的热带环境,仍然有人愿意咀嚼新鲜槟榔来消化食物、消暑。由于槟榔具有成瘾性,咀嚼新鲜槟榔的习惯在这两个地方得以延续。因此,用篮子叶和酸橙吃新鲜槟榔的传统在海南和台湾仍然流行。地理环境限制了长江以南地区槟榔的种植,排斥了槟榔消费群体。福建、广东产的槟榔南下后,只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流行。六朝时期。相反,在福建、广东等槟榔盛产地区,槟榔却是日常咀嚼的“常见饵料”。在湘潭,清朝时期商路发达,商业活动繁盛,吃槟榔的习俗逐渐流传开来。虽然当时不产槟榔,但由于地理优势,吃槟榔的习惯迅速传播开来。由于交通条件较好,贸易逐渐繁荣,南北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清末北槟榔习俗逐渐在民间流传。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所画的清代中国槟榔摊。近代,随着食品工业技术的介入,工业化生产的槟榔因其便于运输、易于储存、风味浓郁、提神醒脑的特点,成为许多辛勤劳动者的爱好。精神。此举风靡全国,打破了环境因素对槟榔饮食习惯的限制。环境差异影响不同地区和季节的槟榔消费模式。这种差异也反映了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的地区环境导致槟榔消费群体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影响各地区槟榔消费规模。同时,我还表明槟榔的消费高度依赖于环境。消费规模和可持续性受生存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2.影响槟榔药用知识形成和“吃槟榔祛瘴”认知的环境因素。 “外事纪事”页面内。杨复《外事实录》云:“若割表皮,煮皮,热之。渗入其中,就会变得像干枣一样坚硬。用古槟榔的灰,吃了它,就会减少能量、食物、白虫,消除槟榔。饮当当饮。”这说明当时的岭南人认识到吃槟榔有理气消食、驱虫的功效。岭南、江南人民咀嚼槟榔,可能与此功效有关。中草药有“药食同源”的传统。槟榔不仅是“食”,还被尊为南方四大药材之首。作为医药,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东汉张仲景的《清桂药诸药方》中就有“四时解五脏热,调芙蓉汤用量方”,其中以槟榔四颗入药。《本草经》(第二编) 作者:[唐]苏静 其他版本:安徽省科技出版局 2005年9月,槟榔开始入药。三国时期,李当之在《药书》中写到槟榔,称其为“槟榔之门”。隋唐时期,槟榔被列入“新材料药物”,列为木材部门的中间产品,并获得批准宋代时,槟榔入药方兴盛,《太平额民洼吉术方》中就有30处槟榔入药,在同时期的其他医书中,如《小儿新书》、《钱之诀》、《苏陈良方》、《薄济方》、《证类本草》等也经常使用槟榔入药。 《点心应用方》、《济生》将药物分为“泻气”、“祛风”、“补虚安”四类。其中,方剂以“泻气”为主,共15方,包括“安息丸”、“丁辰元”、“和胃丸”等,其余15方主要以解积热、消小腹、祛风除虫、补虚损为主。其实,汉末医家已经总结了《名医比尔》云:“槟榔味辛温,无毒。主要用于去谷、逐水、去水、去尸、治白斑等。”后世使用槟榔的方剂,大多都逃不过这样的药性概括。唐宋时期,槟榔还经常用于针灸治疗创伤的方剂中。《盖代秘笈》中记载了以槟榔入药治疗金疮的方剂。另外,《外科文摘》中收录有《生消散》、《生肌散》、《胃极保鲜》中收录有《生楼膏》、《麝香膏》、《白五膏》等处方,均使用槟榔。就像医学一样。 《黄帝内经素问》云:“痛痒疮毒,必治”。 “它属于心。”心主血脉,属火。也有人说,如果阴气不遵循人体的规律,就会出现癫痫和肿胀。王兵曰:“阴气逆,血瘀也。” “因抑郁而积热流脓的病症称为炭疽。”认为疼痛、肿胀主要是营气逆、血气郁滞所致。传统医学认为,槟榔具有理气补虚的功效,值得推广。为什么要用槟榔做药材治疗伤口的药物。唐朝中后期,槟榔还被用来治疗瘴气。在外台秘药中,有“木香犀角肝”的记载,以槟榔入药,建议定期服用。它可以“预防各种致命的瘴气和毒物”。此后,在《苏陈良方》、《传心适用方》、《太平惠民和基础方》、《生机总录汇编》、《瘴疟指南》等医书中频繁使用。见郑全旺认为,槟榔入药治疗瘴气,是因为它具有“行气、祛积、化痰”、“下气”的功效。此证的原理是“气衰”。作者:【唐代】王涛注:高文柱主编:学苑出版社2011年1月 宋代《任治志》《治脚气》中也经常提到槟榔可以治疗脚气。孔塔书中收录了50余种治疗脚气、脚痛的偏方,其中13种以槟榔入药。 “脚气”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张仲景《金匮要论》中记载的“附子”和“鹿米司”两汤中。克弘认为,“脚气”首先产生于岭南,后传入江南。 “风吹来的温暖、潮湿、有毒的空气首先传到脚上,然后从下往上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叫脚气的原因。”唐代孙思邈也认为,脚气的病因主要是“风毒”。又提出,干脚气“风毒在经”,湿脚气“湿脚气毒在经”,仍将脚气与风毒联系起来。据《川崎办处方》,松色王朝表示,用槟榔治疗运动员的风湿病是合理的。那时。因此,李时珍认为槟榔有“祛诸风、降诸气”的功效。点击本版)” 作者:【明代】李时珍 版本:人民医药出版社,1982年11月。吃槟榔可以防瘴气的认识,最早见于郑纲中的《梆》诗。这里的“毒雾浓雾”就是指瘴气。稍后,周去非在《灵外带大》中记载,交子吃槟榔可以防瘴气。瘴气:“(吃槟榔可以防瘴气)。槟榔)防瘴气,下气,消食。如果吃的时间比较长,一定要马上吃。这是吃槟榔时出现戒断反应的最古老记录。另有资料显示,宋代时,礁溪人口服槟榔防治瘴气。罗氏《大教和林录录》中也记载:“岭南人以槟榔代茶,相传有预防瘟疫之效”。这是罗关在岭南的所见所闻,进一步证明槟榔能防治瘴气的知识在岭南早已为人所知。在古代医学文献中,“瘴气”一词最早出现在《神农》中,并出现在《本草纲目》中,瘴气与岭南的关系始于隋唐时期。各种医学文献。他们都宣扬瘴气。理论化,赵元方认为瘴气“生于岭南”,皆为“岭南山岳”,“西源灵章之湿气毒气”。瘴气铭刻于当地风俗之中,隋唐时期,罢官贬官的知识传播开来,岭南瘴气地区的形象也日益加深。电影《奶奶的伯特利》(2017)的静态图像。在雷南人为构建的瘴气区地域意象下,刻板的地域意象促成了瘴气区与瘴气区之间的关联。n 槟榔和瘴气。这种联想出现后,吃槟榔祛瘴的认知也是在槟榔作为祛瘴药的作用和岭南瘴区形象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六朝江学者对槟榔食南的认识,仅着眼于泻气消食。比如,当刘米芝向妻子江哥要槟榔时,江哥开玩笑说:“槟榔可以帮我吃饭,但我总是饿,为什么要这个呢?”这种认识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前面提到的《南方植物》等地理书籍中记载的槟榔的好处。槟榔饮食习惯的传播高度依赖于贸易路线,因此这种饮食习惯很容易因贸易路线的中断而受到干扰。这可能与唐宋以后吃槟榔的习俗在江南消失有关。自从客户唐宋时期江南废除了吃槟榔的习俗,江南士人只能了解角槟榔的消化作用。后来的“吃槟榔防瘴气”的认识,并没有出现在六朝时期江南吃槟榔的士人群体中。早在汉晋时期,医家就开始用槟榔入药,认为槟榔具有理气消食的功效。唐宋以来,槟榔常用作理气、祛风、防瘴的药物。这为后来岭南人认识吃槟榔预防瘴气奠定了基础。最新研究还表明,槟榔中至少含有六种生物碱,包括槟榔碱、槟榔碱、去甲基槟榔碱、去甲基槟榔碱、异去甲基槟榔碱和高槟榔碱。槟榔碱刺激神经系统,给人一种感觉健康,增加唾液分泌,促进胃肠蠕动,促进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医学文献中对槟榔降气消食作用的总结相对应。槟榔原本是一种口服食品,具有“卫生”的含义,因为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反馈与入药的疾病特征是一样的。咀嚼槟榔可以增加咀嚼者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停止咀嚼会导致咀嚼者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其精神状态。因此,长期咀嚼槟榔会产生耐受、渴求、戒断等症状,助长身体对槟榔的依赖。由于“卫生”和咀嚼癖的共同作用,吃槟榔已成为岭南地区普遍的饮食习惯。孩子饮食习惯的出现也是形成的关键与槟榔有关的习惯。此外,槟榔入药的区域趋势也很明显。槟榔最初入药时,只有理气、消食、杀虫的功效。唐宋以后,医家开始越来越重视地方病,并遵循“泻气”、“祛风”的对症思想,用槟榔入药治疗瘴气、脚气等岭南地方病逐渐成为医家的普遍共识。因此,自唐宋以来,槟榔就被普遍用来治疗瘴气、脚气。槟榔自作为理气、祛风、防瘴之药,到槟榔防瘴知识的形成,是人类长期适应生存环境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种文化和生理上的选择ngnan 人根据他们的环境做出反应。这也是隋唐时期岭南瘴气地区的区域形象定型后形成的认知。这种意识是人体对自然环境的感知结果。结果也是环境塑造人类文化行为的过程。它们都体现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中人类行为“形成”的过程。 3、槟榔仪式和人类建造过程的粗俗表达。 《通源》作者:【唐代】杜佑注释,编辑:王文进等版本:中华书局,2016年4月 吃槟榔的习惯是槟榔礼俗形成的基础。传播槟榔药用知识和食用槟榔防瘴知识,是传播槟榔礼俗的关键。最早的槟榔礼俗记载现存文献中的oms可以在《南方植物》第二卷《异物》中引用的文章中找到。 “(槟榔)从临邑出来,别人都认为它是高贵的,婚礼的客人必须先走。如果不安排见面,就用相互仇恨的话。”这里,“槟榔嫁”是临沂的习俗。后来在《通典》中,杜宇还提到,“葛鲁鲁王国”的婚礼习俗是“第一次求婚时只能用槟榔作为礼物”,而这种登记也是域外的习俗。到了宋末,槟榔已逐渐成为“中华风俗”。例如,陈敬一在《泉芳北图》中描述了中国南方的一种习俗:“男子聘用女子,必以槟榔为礼,宾客相聚,必先带槟榔,若不用槟榔,则互相憎恨。”宋代吴谦被流放到浑州时曾写道:“巫师用他们的”这也解释了中国赠送槟榔的习俗。咸州民间传说。从一般情况来看,“聘槟榔”应该是最主要的槟榔礼仪形式,明清时期在两广地区最为普遍。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泗州,“嫁娶不用媒人,而用槟榔”,广东南雄县“嫁娶用槟榔”,惠州县“旧婚订婚用槟榔”,潮州县“鸽果为喜食,作结婚贺礼”。所有槟榔在婚礼仪式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富川、平乐、恭城、武宣、北流、雷州、电白、灵山、增城、阳江、广宁、化州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县在广东省的凤川、华化、新会、象山、德清、茂名、吴川、清远、信宜、阳山、恩平等地也有承包槟榔的习俗。 《采槟榔图》(清代,不详画家)的一部分,描绘了云南省少数民族采摘槟榔的情景。近代以来,广东、广西两省食用槟榔的人数明显减少。与此同时,用槟榔招人的习俗在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逐渐消失。但海南仍然有这样的遗产。在海南省一些市州,点名聘人仍被称为“讨槟榔”或“摘槟榔”,并仍以槟榔作为礼品。作为礼物,槟榔也经常出现在葬礼上。例如,在云南天岳,人们用槟榔和甘蔗籽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我在广西北流,人们用槟榔香和蜡烛表达哀悼。在广东省澄海市,“慰问”用槟榔和蜡烛来表达感情。 “槟榔,槟榔。”福建省泉州,“las nueces de betel se utilizan como obsequio a los amigos del pueblo para celebrar la buena o la mala suerte”。在海南岛的一些市县,槟榔在丧葬活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婚礼的服装和葬礼、宴会的邀请和团体的各种活动中的“公社”原则都是重要的。分享槟榔的可能性为习惯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这是槟榔的“自定义”属性。清王朝的惨痛教训,湖南湘潭的槟榔人物编号和其他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随后,“槟榔”逐渐融入湘潭人的礼俗之中。例如,湘潭过年时会赠送槟榔作为拜年礼物。槟榔也可作为结婚礼物水果。在许多礼仪场合,槟榔被用作馈赠宾客的礼物。这与广东、福建、海南等省的槟榔习俗十分相似。 《福建通志》(编)作者:【明代】黄忠昭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槟榔的饮食习惯不能与槟榔的礼仪习俗划等号。槟榔礼俗强调槟榔作为馈赠水果的文化作用。在礼俗中,槟榔参与仪式。作为一种饮食习惯,槟榔无非是一种口头传统。 coStumbres 是依赖于社区成员必须遵循的传统力量的标准化行为。形成槟榔礼仪也受到传统力量的影响。关于文化 作者:[英文]马林诺夫斯基 译者:费孝通 版本:华夏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1月 当一个社区有共同的饮食习惯时,这些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该社区大多数成员行为的驱动力。槟榔礼仪的形成就是在这些社区习俗的推动下形成的。由于槟榔产于岭南及西南部分地区,因此槟榔被用作辟瘴、防疫的手段。在某些虫害肆虐的环境下,“送槟榔”逐渐成为一种社交礼仪,让槟榔变得“可分享”。这种“共享性”是建立在与环境互动的基础上的。槟榔的共享使其成为人们日常交往中的“社会共享物”。热南槟榔习惯的形成背后有着明显的内在驱动力。换句话说,人们吃槟榔是出于“卫生”的原因s,出于抵抗瘟疫的需要。这是宋代相信槟榔能祛瘴的信念所驱动的“个人自觉行为”。而当这种“个人自觉行动”演变为“集体自觉行动”,即社会“大多数”认识到槟榔可以防治瘴气时,槟榔礼俗就诞生了。这个逻辑也可以解释湖南湘潭等地区槟榔习惯的形成。湘潭槟榔:战争疫病说、药材市场说、风水说、槟榔仙人说。其中,战争瘟疫说、药市说、槟榔仙说等都与瘟疫流行有关。这表明湘潭人吃槟榔,很可能能抵抗瘟疫。因此,凭借靠近岭南、有商路支撑的优势,吃槟榔在湘潭人中越来越普遍。随着普通人的成长在消费群体中,槟榔逐渐成为湘潭人的“社交交换对象”。吃槟榔、“送槟榔”逐渐成为各种社会场合的“自觉集体行为”,并作为送礼融入当地礼仪活动,从而形成了当地槟榔标签。其世代逻辑与热南地区槟榔礼俗的世代并无不同。 198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流行歌曲《摘槟榔》(张野演唱)做背景。由于槟榔不是土特产,所以江南地区槟榔的消费者仅限于社会上的少数贵族。吃槟榔的习俗尚未形成相应的群体基础。六朝时期,江南士人认识到吃槟榔仅限于消气消化食物的目的。而且,在江南,吃槟榔的习俗已经消失了自宋代以来,槟榔习俗的推动力微乎其微。这就是原因。在江南地区,有吃槟榔的习俗,但没有吃槟榔的习俗。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由于地域限制,本地不产槟榔,只在北京的部分人群中流行。清末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北京人吃槟榔的习惯逐渐衰落,并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辛亥革命后,北京吃槟榔的习俗就被废弃了。吃槟榔的习俗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之后才形成“自觉的集体行动”并进入仪式。与吃槟榔的习惯相比,吃槟榔的习惯分布更为广泛。在史前时期,吃槟榔的习俗在北方和北方都盛行。南方。如今,吃槟榔的习惯在全国各地都可见一斑,但吃槟榔的习惯仅分布在海南省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区。槟榔习惯的形成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文化反应。然而,很多人并不需要吃槟榔来养成吃槟榔的习惯。借助食品工业化,槟榔失去了传统形象,以其浓郁的风味和引人注目的包装成为可以与香烟区别的国民“零食”。全国各地都吃槟榔。 1930 年代,越南,摘自阮彭将军的《卖槟榔的人》。国内外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人口是槟榔消费的主要来源。中国有句俗话:“槟榔与烟草相结合,百味无穷”。国内生产槟榔已经不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槟榔的消费在其他方面已经超越了传统时代地理环境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人又会吃槟榔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是目前的槟榔消费行为只把槟榔当成一种振奋精神、缓解疲劳、对生理有刺激作用的消遣。得益于现代食品工业,槟榔也被用作口服零食。口服槟榔的目的不再是预防瘴气的卫生手段。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槟榔对人体健康有害。它甚至被认为具有致癌性。此外,现代槟榔消费者性别失衡也是槟榔难以渗透社会习俗的重要原因。根据研究,在t湖南省长沙市和湘潭市是槟榔消费较多的地区,两市城镇居民中,有76.7%的男性和56.2%的女性咀嚼槟榔。在调查的男性样本中,有31.4%经常咀嚼槟榔,而女性样本中这一比例仅为6.7%,远低于男性样本。 2018年,台湾18岁以上男性嚼槟榔的比例为6.2%,女性仅为0.2%,远低于男性。 40岁至49岁人群中,嚼槟榔的比例最高,为5.4%,其中男性占10.7%,女性占0.2%。差距就更加明显了。电视剧《结婚公告》(1998)剧照。据笔者观察,日常生活中嚼槟榔的人以男性居多。此外,由于现代人追求洁白牙齿的审美观,大多数女性拒绝咀嚼槟榔,甚至厌恶男性咀嚼槟榔。有ar其他地区没有相关统计,但情况应该类似。槟榔消费者性别失衡 这意味着吃槟榔并不是这个社区常见的饮食习惯。因此,大多数社区成员的行为没有规范的动力,槟榔很难融入现代礼仪和习俗。换句话说,吃槟榔的习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吃槟榔的习惯却在减少。毫无疑问,传统时期槟榔习俗的兴衰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以雷南为例。清代以前,岭南是一片瘴气之地。槟榔因其具有祛除瘴气的功效,很快成为岭南地区流行的食品。消除瘴气的关键在于改造产生瘴气的地理环境。元明以来,岭南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岭南经济的深化发展和南迁北迁人口的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明清时期的气候干冷趋势,也引起了岭南气候湿热的变化,产生了瘴气。清朝以后,岭南瘴气地区大部分消失。随着现代西药的传入,槟榔、槟榔等传统防瘴药材,逐渐被奎宁、枸橼酸哌嗪、青霉素等高效廉价的抗寄生虫、抑菌药物所取代。岭南人不再需要吃槟榔来防瘴气,吃槟榔的人数急剧减少。结果,嚼槟榔脱离了群体结构,在整个社会层面不再普遍。槟榔习惯也失去了“集体意识”土壤。此外,由于“重大变化“在现代的传统习俗中,原本繁琐的婚丧嫁娶等习俗已逐渐简化,槟榔很难融入到更具社会属性的婚丧习俗中。当地传统吃槟榔婚礼的六礼已被简化得一应俱全,让槟榔婚礼成为过去式。传统时代赋予槟榔的各种意义正在逐渐消失,其背后的“人地互动”元素也在逐渐淡化。因此,槟榔风俗在热南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这也是热南自近代以来槟榔和槟榔习俗衰落的原因。 四、结语槟榔文化属性的生成和演变本质上是历史时空中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文化诠释过程。l 槟榔作为食品、药物和习俗的属性并不是一朝一夕显现出来的。它们是在人类活动和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从“自然”到“文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也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适应生存和文化建构的过程。槟榔食品属性的形成,标志着槟榔作为一种类似兴奋剂、具有减气、消食作用的热带水果正式纳入人与环境相互作用领域。它是人类在适应生存环境过程中做出的经验选择。但槟榔最初在岭南人中很流行,因为槟榔可以在湿热的环境中补充能量,所以他们开始每天咀嚼槟榔。后来,随着南北之间的货物和知识交流更加频繁,有关国家的记录也被传播开来。岭南的槟榔与中医知识。随着知识的传播,吃槟榔的习俗也随之传播。但由于槟榔生长环境的限制,槟榔的习惯只在六朝时期的江南士大夫和清代的贵族中短暂流行过。近代,随着食品工业化的发展,槟榔的习性已经成功超越了环境因素的限制。槟榔入药是槟榔的文化重要性。将经验实践转化为制度化知识。随着各种方剂书籍和本草的传播,槟榔的药用知识已经系统化。但对于脚气、瘴气等局部疾病,仍很难打破用方剂或草药治疗局部疾病的观念,成为灵丹妙药。通过对槟榔的系统认识,人类应对生活环境带来的生理挑战。槟榔入药后,其物质价值也随之增加,赋予其仪式化以认知前提和合理性。与槟榔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相比,槟榔的仪式化更能凸显槟榔栽培建设过程中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伯特利仪式训练不能通过简单的人际模仿或仪式模仿来获得。自然环境决定了槟榔的供应量和食用槟榔的人。热南槟榔的普及,促进了槟榔饮食习惯在当地社区的广泛出现和共同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槟榔习惯。槟榔标签不是文化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同质化的结果基于适应环境需要的集体消费行为的化。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设行动。吃槟榔的风俗曾在江南、江北的一些地区短暂出现过,但由于槟榔食用没有同质化,上述地区并没有形成槟榔仪式和习俗,更不用说模仿岭南等地的槟榔仪式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塑造,不仅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应激”反应上,更在更深层次上对人类社会文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人地互动”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环境决定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些就是基于上述的独立努力以及这些独立的努力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影响。通过“人地互动”的视角来解构槟榔的文化属性,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塑造作用,也可以看到人类与环境在人类文化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人地互动”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基于单一观念推断文化行为模式的现有逻辑,也让我们发现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微妙方面。 【来源】于王仁政 作者:王仁政(南开大学历史学部中国史博士生)